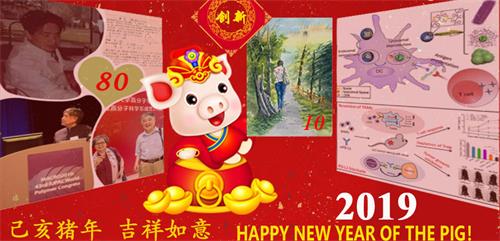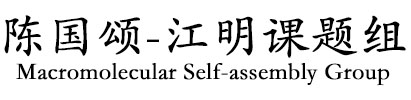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江明老师“My Life in the Golden Age of Polymers.”系列故事第二篇网络发布 桑榆恰是叙旧时之二 我学术生涯里的领带情结 江 明
15年前,陈国颂[1]博士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就职复旦大学,成为我的同事和“战友”。基于她的努力和成就,加上她突出的“学术外交”能力,几年前,她在国际高分子学术界已很活跃,不断受邀出国开会,讲学。但是,全球性的新冠疫情迫使她失去了和国际同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达三年之久。据我观察,她被憋得太难受了。
我是1979年4月赴英访学的,7月进入Liverpool(利物浦)大学实验室。到了1980年初,我在实验室的工作已做了半年多,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心里有些着急。不过由于我把实验外一切可用的时间都用来苦读Polymer Blends (聚合物共混物)这一陌生领域的大量文献,对其中的基本问题有了些了解,我迫切希望有向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当面求教的机会。这时,我的英国合作导师Geoffrey Eastmond[2](我们常叫他 ‘Geoff’)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一场 HPRG 会议,主题就是Polymer Blends。他还给我看了已落实的会议报告人的名单,那都是在文献中已很熟悉的,如今叫做“牛人”或“大咖”的人物,不过我一位都没见过。这会议对我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会议的注册和食宿费用对我这样的公派访问学者来说,自己是完全无力负担的。而Geoff课题组一直是财源紧张,爱莫能助。于是我只好心怀侥幸,向我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提出了经费申请,不料申请竟然很快就批准了。那时的访问学者多数由于语言的困难,对于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是保守的,甚至是胆怯的。后来我才知道,虽然使馆有经费支持访问学者参加学术会议,但申请者寥寥。所以说当时我的这个做法可算是相当“前卫”的了。
图1. Manor House Hotel, Moretonhampstead, Devon, HPRG会址(取自网络)
图2. Moretonhampstead大教堂休息室、会议的报告厅(取自网络)
HPRG会议开会的方式很是特别,与美国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高登研究会议)[3]很像,只有邀请报告,每场报告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在1小时左右。因此,受邀的报告人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每天上午和傍晚演讲,下午休息,打高尔夫球和钓鱼。为了鼓励无拘束的自由讨论,会议不提供论文集和任何文字记录,但为每位参会者赠送一条领带。另外,会址特意选得远离闹市,为参会学者营造出钻研学术的“世外桃源”。
邀请报告人多数都是我已熟读的文章的作者,向往久矣。现在可以一睹其风采甚至个别交谈,很是兴奋。这些报告人中有多人对我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如斯坦福大学的C. Frank、麻省大学的F. Karasz、里海大学的L. Sperling、贝尔实验室的T. K. Kwei(他后来去了高分子知名学府纽约理工大学)、米德兰大分子研究所的D. Meier、以及法国上阿尔萨斯大学的G. Riess等等。有趣的是,这些演讲者都是中年学者,未见特别资深的前辈,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年代,Polymer Blends确实还处于新开发的前沿领域的缘故。得益于我以前对报告人的工作有了大概了解,加之每天会议的下午,在洋人同行尽情享受高尔夫的时候,我总是在加紧消化报告和阅读文献,三天的会议开完,我就像是修读了“intensive course(强化学习班)”一样,收获满满。我当时的英语口语还很不流利,又是研究资历最浅的参会者,似乎只能“谨言慎行”。但强烈的学习欲望还是促使我大胆地与一些报告人主动接触和交谈。那时国门刚刚打开,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参加HPRG系列会议的中国大陆学者,也可能是演讲人接触的中国学者第一人,所以在交谈中我可以察觉到他们对我很是好奇。虽然在学术上我很少能为对方带来什么,但我的好学与真诚还是让我赢得了友谊,交上了多位异国学术界朋友。5月2日,会议结束,我搭上了Geoff的汽车与几位参会的利物浦大学的教授一起北上返校。虽然从Devon到Liverpool贯穿了半个英格兰,一共也就几个小时车程。这是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4],几百公里的路程中没有遇到一个“红绿灯”,内心为之震撼!不过此时的我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来自泱泱大国的堂堂访问学者可不想被外国同行看作“乡下人”。
1981年我回国后很快建立了课题组,经几年努力,在聚合物相容性方面已取得了拿得上台面的成果。1986年夏,我在英国Calvert博士的支持下获得去美国MIT(麻省理工大学)短期合作科研的机会。因为有了些底气与同行交流,我当然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多走访几所美国大学,可我又遇到了经费的难题:MIT只提供我在该校的研究和生活费用;但我当时在国内的月工资约合20美元,想自费出访无异于做梦。还有一条路,就是争取受访者的资助。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国际上还是寂寂无名的副教授来说,要得到名校名教授的邀请确实不易。这时我自然想到了在HPRG会上认识的几位新朋友。我于是给Sperling、Kwei、Frank 和 Karasz分别写了信,开头都是“亲爱的某某教授,我想几年前我们在HPRG会上的相见仍在你的记忆中……”,如此“套近乎”竟然还真的有效,这四位教授全都回信热情邀请,还慷慨表示负担我的当地食宿和城市间的飞机票。这样,我成功访问了斯坦福大学,麻省大学,纽约理工大学和里海大学。同时,我还利用了先前在国内接待来访美国学者的“关系”,应邀访问了纽约州立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辛辛那提(Cincinnati)大学以及杜邦公司研究中心。在这些“顺访”活动中,我做了七场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和赞扬,还与杜邦公司达成了一项对方出资的研究协议。我访问的多位教授们说,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确实,80年代中期,在国外进行这样的系列讲学活动的我国高分子学者是极少的。访问和讲学的成功加深了我与许多名家同行的相互了解,我也开始步入到这一领域研究学者圈子的中心。显然,这次出访能做得如此充实和圆满,HPRG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我1980年的那次参会,那一切就不会这么顺利了。
如果说HPRG的学术活动的方式是仿效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的话,会议向每位参会者发一条固定花式(Pattern)的领带,就完全是一项“创新”之举了。记得我在1980年参会注册时未见会议论文preprints(预印本),只领到一条黑底黄花的领带,颇为不解。Geoff就告诉我:“这个会有个传统,向参会者赠送领带。领带的颜色可以改变,但Pattern永远不变……”领带的图案是,一行行规则排列的锯齿形线条,其间交替排列着成行的狮子(图3)。很明显,这锯齿形线条就是代表拉直了的高分子链,而狮群就是英国的象征。所以这领带的关键词就两个:高分子,英国。
图3. 1980年,第20届HPRG的会议领带
既然这领带有独特的学术含义,我自然珍爱。1988年,我首次参加IUPAC Macro大会(日本京都)就佩戴了它。当时坐我左边的正是我在HPRG会议上认识的斯坦福大学的Frank教授(图4)。其实,早在1980年2月2日,我国驻英使馆参赞来利物浦设宴招待访问学者的导师时,我的“大老板”,英国皇家学会院士C. H. Bamford[5]教授应邀正装出席,也佩戴了这领带(图5)。这领带也是Geoff的最爱,常见他在办公室戴着(图6)。
图4. 1988年我佩戴会议领带参加IUPAC Macro大会,我的左边是斯坦福大学的Curtis W. Frank教授,右边为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的 Saverio Russo教授
图5. 我的大导师Bamford教授佩戴会议领带参加中国大使馆晚宴(1980),我陪同
图6. 我与佩戴会议领带的合作导师G. Eastmond教授讨论课题;后排是课题组博士后M. Malinconico博士,后担任意大利聚合物、复合材料和生物材料研究所 (IPCB-CNR) 所长
High Polymer Research Group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8年,是当时英国高分子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知名学者成立的学术团体,其使命是通过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支持聚合物科学研究。早在1961年就在茅镇举办了第一次会议。这首次会议的第一位报告人就是高分子界蜚声环球的Paul Flory[6](他当时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化学奖),这似乎就为该系列会议定下了高水准的标杆。自1961年起,会议每年举办一次。我1980年参加的是第20届,今年国颂参加的已是第61届[7]了。
国颂如约在会后给我带来了今年的HPRG会议领带,还是那代表着“高分子—英国”的图案,还是那黑底金色的花纹,43年过去,两条领带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国颂还得到了一条会议丝巾,仍然沿用了同样的图案(图7)。这显然是因为如今参会的女性科学家越来越多的缘故,还说不上与“女权主义”有什么关联吧。经过几十年的坚守,领带,这种不起眼的小物件,竟成了HPRG学术地位的象征,成为高分子学者之间的一个相互沟通的标记。大家即使不相识,但是看到对方佩戴了相同的领带都会心一笑,“你也参加过HPRG呀?”近日,我们查阅HPRG的官方网页,大有所获。这里不但记载着HPRG的来源和历史变迁;还有,自1961年起,HPRG的61届会议的科学主题、时间、地点、邀请报告人、报告题目,甚至报告主持人全部有详细的完整记录。英国科学家们对科学传承的尊重甚至敬畏之情,令人肃然起敬。我不由得想到我们自己。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查阅学会、学会专业委员会、系列会议的网页,页面设计的都很漂亮,甚至华美;但如果从中想得到这些学会或系列会议的历史资料,往往都很失望,见到的常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历史的新生儿。不能不令人感叹不已!
图7. 两条相隔43年的HPRG会议领带(左图)与今年的HPRG会议丝巾(右图)
陈国颂这次参加的第61届HPRG的主题是Polymers in Water。她是大会报告人,也是仅有的一位来自中国的报告人。意味深长的是她以43年前我与Geoff佩戴会议领带的照片作为报告的开场白(图8)。我和她参会的年纪相仿,都是40岁过点,似乎一切都很自然。然而当年我是一名学术资历最浅的听众,如今她是受邀的大会报告人,这个对比是强烈的,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视为中国高分子过去40年巨变的反映。国颂能够受邀做大会报告,与她特别关注和珍惜国际学术交流不无关系。记得2012年我们一同去英国Warwick(华威)大学参加高分子大会,这是我最后一次,但是她回国工作后第一次出国开会,所以对我们“一老一少”来说,都很有意义。我开完会就回国了,她特地多留了一个星期。虽然是第一次去英国,她这一周哪里也没去,总是天天泡在知名的Warwick高分子的新建实验室里,收集了这个实验室的许多资料,为我们系在江湾校区新大楼里实验室的规划布局做准备。她还和那里的教授与学生们深入交流,搞得很熟,特别是与Rachel O'Reilly[8]教授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以为,对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视、珍惜和运用自如,是国颂特别明显的学术品格。这使她在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后,很快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她在2018年即受聘为ACS Macro Letters的副主编,便是一例。我不敢说陈国颂的这个特点是来自什么基因传承,但确实是与我的理念和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图8. 陈国颂在第61届HPRG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图9. HPRG 2023的三位女教授:陈国颂(后排,大会报告人),伯明翰大学的Rachel O'Reilly(前左,会议组织者)、美国特拉华大学的Arthi Jayaraman(前右,大会报告人)。注意陈和Rachel佩戴会议丝巾;据说A J教授认为会议给女士赠送丝巾有对女性的“歧视”之嫌,因此选择仍然选戴领带,但用女性围巾的方式佩戴。
在本文完成初稿之际,2023年的10月29日,在何军坡[9]教授的安排下,我与中国高分子人的老朋友,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希腊教授Nikos Hadjichristidis一起在上海新天地共餐和畅叙(图10)。他已80岁了,目前还在领导着一个20人的Group,仍在满世界参会,令人叹服。他自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一直在高分子化学的世界前沿工作,已逾50年。如今有如此丰富经历且有超强朋友圈而仍然健在者,实属稀有。听他讲科坛背后的故事乃至国际同行“大佬”之间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此词并不夸张),是极有兴味的。我对他坦言,他今后对高分子的最大贡献,不应再是大分子论文了,而应是凝聚了鲜活故事和人物轶事的回忆录。他连连称是,真值得期待。更有趣的是,谈到HPRG会议,他说他有多条会议领带!第二天他飞回沙特后立刻给我发来了照片,这里有我第一次见到的粉红底色的“版本”(图11)。他说回到希腊家中还会再将他的HPRG领带“收藏”拍照发给我。看来HPRG领带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图10. 我与Nikos Hadjichristidis教授在上海新天地畅叙
图11. Nikos Hadjichristidis教授珍藏的HPRG会议领带
[8] Rachel O'Reilly,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高分子化学家,《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副主编。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