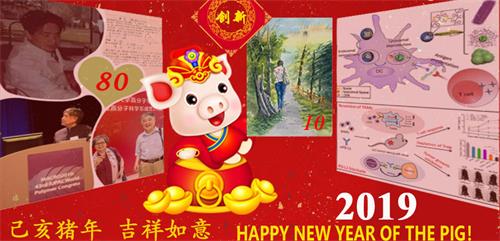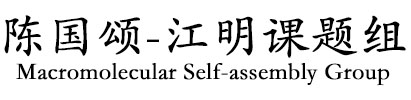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江明老师“My Life in the Golden Age of Polymers.”系列故事第三篇网络发布 桑榆恰是叙旧时之三
科研路上遇贵人:魏格纳教授
江 明
谨以此文庆贺魏格纳教授84岁华诞 !
有了《旦苑晨钟》这个公众号平台,我的《桑榆叙旧》系列短文觅得了更多知音。前两篇我分别讲了与百年前英国大亨雷士德的情缘,以及两代高分子人的共同的“领带情结”,都有5000多人阅读。虽然我知道好多人并没有读完,因为在这个快阅读的年代,几千字的文章还是长了。不过这个数据还是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应该好好写下去。在我的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师长,学友,同行和朋友都值得记叙。打算先写其中的洋人朋友,我首先想到的是德国Gerhard Wegner(魏格纳)教授(图1)。他比我小两岁,不是我的导师,我们甚至没有多少学术上的交集,也没有共同发表过文章。但是Wegner教授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可以称为我科研路上的“贵人”。
图1. Gerhard Wegner教授(1940— ),取自网络
我早在1981年就认识Wegner教授了。那年4月我从英国完成两年的访学回到复旦大学。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外国同行纷至沓来。接待外国教授政治上早已没有障碍,但在语言交流方面却是困难重重。当时除个别人,广大教师和研究生是没有能够听懂英语学术报告的,所以必须要翻译。我们教研室能够胜任学术报告翻译任务的也只有于同隐先生[1],可是于先生当时已经60多岁了,让他为外国教授,特别是为青年学者做口译,看上去很不得体,他也很累。所以我一回来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到了10月,我听说德国的Wegner教授要来访问,很开心。我知道他来自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这是施陶丁格[2](Staudinger)创建高分子的地方,是世界高分子科学的“发源地”。Wegner是德国高分子界的一颗新星,35岁就当上了教授,是弗莱堡高分子研究所的所长,在国际高分子界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10月12-13日,Wegner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做两场报告,这是我“预习”的好机会,所以我到有机所“先听为快”。15日他到我们复旦做报告,主题是“德国的高分子研究”。因为我在有机所已经听过一遍,所以我的口译非常顺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所接触到的外国访问教授中,我对Wegner教授的演讲特别欣赏,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出众;他的英文表达,我觉得可以说是个范例。他讲英文流利如母语,发音清晰,徐疾有度,而且出口成章。把他的话记录下来,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听这样的报告,确是很享受。再者,他身材魁梧,面目和善,儒雅潇洒,一派欧洲绅士风度,显现出非凡魅力。刚回国那几年我接待过多位大牌教授,Wegner给我留下的印象独特而美好。
图2. 1984年Wegner教授给我的邀请信
[1] 于同隐 (1917.9—2017.2),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者。 [2] 施陶丁格(1881—1965),德国化学家,大分子概念的提出者,195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3] 相容(溶)性的非专业解释:水和酒精是相容的,水和油是不相容的。高分子也一样,有些高分子之间是相容的,有些不相容。高分子相容性的研究就是探究其中的规律并用于高分子材料的设计改性。
Wegner的回信是这样开始的:“我记得(1981年)访问复旦大学,这是我在你们国家各地访问的亮点之一。事实上,我迫切想知道你和你的活跃的课题组自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进展。”这两句话立刻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似乎是对我说,这个访问并不是我一定要求他做什么,而是他自己也很需要了解我们的进展。他还在信中说,我邀请你来访问我们在美因茨的研究所,可以停留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去参观DKI(德国国家塑料研究所),那里距离美因茨只有30分钟火车的行程。他信中又继续跟我说:“我可以帮助安排你去弗莱堡访问,我想你在那里待两天是比较合适的,其中一天作学术访问,另外一天可以参观游览。那里很可能是由两位教授中的一位来接待你,就是Cantow(康托)教授或Eisenbach(爱森巴赫)教授。”显然,他是希望我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时间,得到最大的收益。真正是善解人意呀!当然,他还说:“如果你在我们研究所做一个学术报告总结你和你们研究小组最近的工作,我们将会非常感谢。”另外,他表示会支持我在美因茨的全部费用以及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通读下来,你是否也能体会到,这不是一封例行公事地接受访问的回信。如此地体贴入微,读来真是如浴春风。其实,给我这样的回答,对Wegner教授来讲是很自然的,想来他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是对我来说,这信充满了对一个刚步入科学讲堂的异国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令人难以忘怀。 因为手续的繁杂和其它各种原因,我这次访问一直到1984年的12月初才成行。我于12月3日和王老师一同去杜塞尔多夫,然后在那里做了大概两个星期的工作讨论和操作培训。12月16日离开那里乘火车到美因茨,到时天色已晚。Wegner教授在此之前已经电话与我联系过,他说他帮我订的旅馆叫Hammer。他要我不用担心找不到它,说“你走出车站出口(美因茨虽是世界著名的化学研究中心,但城小,火车站只有唯一的进出口),看到马路正对面的一座小楼就是。”事实果然如此,当晚我顺利安顿下来了。17日的清早我就来到了美因茨大学校园,那时研究所的大楼还没建造,他们临时“蜗居”在大学校园内的一座小楼里(图3)。连续三天的访问,Wegner教授给我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动计划表。我完全按照计划,按时见到了研究所的另外两位大教授,H Spiess和E Fischer。我还与他们组里面的课题组长都一一交谈。这个研究所虽然刚刚成立,但是聚集了权威的学者和非常精干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研究的最前沿。与他们的交流,当然使我大开眼界。在他们当中,一位叫做 Hellmann(赫尔曼)的博士后已经看到我发表的论文,对我的工作表现出特别的兴趣。19日的这一天就是访问的高潮了,11:00我有机会去见到了美因茨大学的H Ringsdorf(林斯托夫)教授,就是张希[4]老师后来的博士导师,是我们中国高分子界的好朋友,我以后还会专门写到他。下午13:00,我开始了我在海外的第一个Seminar (科学报告),Wegner教授亲自主持。虽然是第一次,由于准备得充分,我讲得是比较从容的。演讲的显示工具是当时国际通用的幻灯片放映(图4)。报告以后讨论热烈,Hellmann博士接连提问。后来他沿着我做的这个方向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成为“小同行”,且成为引用我们论文的“大户”。我演讲完毕时,居然没有掌声,但却突然响起乒乒乓乓的敲桌子声,我真是吓了一跳。但从他们投来的满意的目光里,我马上意识到,原来这是德国特色的对演讲人赞赏的表示方式。
图3. 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取自网络
图4. 我报告用的幻灯片,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显示方式
[4] 张希,高分子和超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吉林大学校长。1992年获吉林大学博士学位,师从沈家骢院士和德国美因茨大学H Ringsdorf教授。
在我的小笔记本里,我记下了这紧张又十分有意义的一天(图5)。
图5. 1984年12月19日的日记
在美因茨,Wegner教授招待我一顿晚餐,这是一般的惯例。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他竟然选的是南斯拉夫餐馆。那天吃的什么,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是和教授的谈话我还是有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彼此已经没有了陌生感,我也就没有顾虑地向他道出了我存在已久的疑问。我说在德国半个多月,看了很多,惊叹于德国的先进。朋友们还告诉我,许多高水平的设施二战以前就有了,而德国人对世界思想文明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的。但是,30-40年代的德国人怎么会让希特勒这样的魔鬼统治了国家,而且把灾难推向全世界?……他沉思片刻才做出了回答,我至今还记得教授那严肃而沉重的眼神。当然,不可避免地,他问起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去英国留学,开始做研究,我多少也讲了一点自己的故事。 12月20日,我乘火车到了弗莱堡,朝拜了世界高分子的发源地。见到了Cantow教授,他的大名我在60年代就晓得了,因为在钱人元先生写的高分子溶液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过。因此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就有一种亲切感。他同样给我安排了紧张又充实的访问程序,我按时与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了交流(图6)。教授照例请我吃饭。这回用餐时我们谈了什么,完全记不得了。但吃了什么,却印象深刻。他说“请你吃一个标准的德国餐。”起先服务员给我们一人一套小锅和油灯。我想“嗯,火锅,这德国餐可以接受。”不料服务员上来没有给锅里加水,却加了油!当油加热到有点起烟时,我跟着教授的示范动作,把自己面前的牛肉、羊肉、猪肉一一开涮。台面上几乎没有素菜,我吃起来感到实在太油腻了。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最多只完成了1/3左右。可是坐在我对面的Cantow教授,要比我大十几岁,他轻松光盘,真使我自叹不如。21日中午我做了报告,内容和在美因茨时是一样的,讲得就更轻松自如了。所不同的是在弗莱堡有三位中国的访问学者在,其中一位就是我认识的化学所的陈寿羲老师。晚上他们邀请我在他们住所里面吃了中国菜,大家聊天到很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三位都说,在这里很少中国学者来做报告,虽然也有个别的来过,但是他们觉得效果不很理想。这次我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外国人听了很欣赏,所以桌子敲得很响,这给大家“长了脸”。这几句话自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图6. 弗莱堡大学Cantow教授为我安排的日程表
由于Wegner教授的精心安排,我第一次出国的学术访问很圆满地结束了。其实我与Wegner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后来在1986年,他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参加中德双边的高分子会议。在会议期间,他邀请我第二年到他们研究所做两个月的访问。我问他,你要我去做什么?很意外,他说“随便你做什么。”为此我纳闷了很久,以我当时的研究水平,我实在是很难为对方作出什么贡献,但Wegner为什么热情相邀呢?过后很多年,我与教授有了更多的相处,才逐步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个要留到以后的文章里再谈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