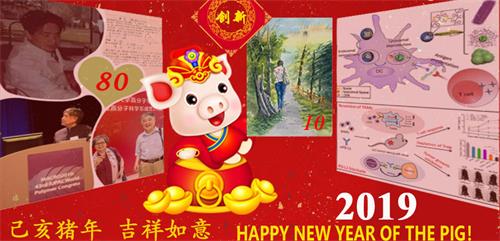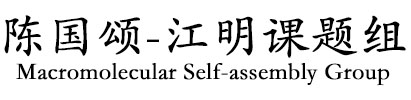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1 —列日缘份
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1
—列日缘份
王锦山
在美感恩节度假的第二天,好友义松[1]在微信小群里转发了“旦苑晨钟” 创刊号江明院士的“桑榆恰是叙旧时之二 我学术生涯里的领带情结”,并@我说,江老师希望我写点东西。 很久没写过这样的文字了。与江老师微信后,我断断续续想了一天,写什么呢?明年是我发现“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ATRP)30周年,本来也想写点与ATRP有关的故事,纪念一下。 粗看起来,列日大学[2]似乎与ATRP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列日大学,我的博士导师Philippe Teyssie教授使我人生发生了根本蜕变,并全副武装了我日后构思和发现ATRP的大脑和双手;也是在列日,我与江老师初次结缘。 那就写篇“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1,列日缘份”! 32年前的1991年的某一天,在Teyssie教授的副手Jerome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江老师,记得那天江老师是应邀前来做“聚合物共混(Polymer Blends)”学术报告的。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能在遥远偏僻的外域小城见到同胞大教授,其兴奋激动之情真的难以言表。尤是刚到Teyssie实验室不久,之前在复旦大学做过博后研究的义松,见到复旦过来的老师,更是激动不已。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江老师的精彩演讲,以及他那特有的、彼时中国学者难得一见的潇洒和自信,至今历历在目。让我和义松再感动一回的是,江老师满足了我们的小心愿,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家(图1,图2)用中国菜招待了老乡江老师[3]。
图2. 离开列日12年后,我第一次回比利时列日时,与我的双胞胎儿子在 25,Rue De Fragnee门前的合影 [1] 于义松,华东理工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我同校同专业77级学兄,几十年的挚友。1987.12–1989.12义松师从复旦于同隐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在Teyssie教授名下读博时,义松是Teyssie的助理研究员(1991–1994)。义松在Tessyie实验室从事的导电共混高分子、双阴离子引发剂、活性阴离子聚合合成热塑性弹性体等研究均做出了世界顶级水平的工作。 [2] 列日大学 (法文:Université de Liège;英文:University of Liege),成立于1817年(中国当时是清朝嘉庆二十二年,比利时王国还没成立),位于比利时的第三大城市列日市(法语区),是欧洲最早成立的公立高等学府之一。培养了比利时天体物理学家Pol Swings,197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Albert Claude等杰出人士。Teyssie教授实验室位于列日市中心以南约10公里的Sart-Tilman(萨尔·蒂尔曼)山上校区理学院大楼内(我们当时都称上山),周边是数百公顷的绿地和森林,环境极其优美。我、义松、田东及其他中国留学生经常饭后在山上森林中散步,有时还饶有兴致的扔几块石头,从高高的野树上打下野生梨、苹果吃。 [3] 我是泰州人。出国前泰州市是扬州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我和江老师(扬州人)算是老乡。 读过江老师公众号大作,我惊喜发现,在列日这个点上,我和江老师又多了一层缘分。江老师早年在英国Liverpool大学Geoffrey Eastmond教授实验室整整二年,而我在列日Teyssie实验室曾花三周时间手把手教会了Eastmond教授的美女博士生Paula Schofield,用阴离子技术合成她博士课题所需的两性嵌段共聚物样品。后来,Paula把我推荐给她在美国柯达公司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当经理的父亲,Dr. Ed Schofield(图3)。我于97年年初举家搬迁到了柯达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入职柯达。Paula她爸早年也是Liverpool大学博士毕业生,他的博士论文课题还是活性自由基聚合。正是直接和间接的列日之缘,我和Paula、Ed、还有Ed的华人太太都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说实话,要不是读博,我很难会去列日这个小镇,更难想象与它结缘如此多,如此深。 上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国人振兴中华的热情却无比高涨,很多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国内大干一场。85年初,我硕士毕业留校后,就满怀热情投身到了时任校长陈敏恒教授推行的轰动全国的教育改革中。作为他的青年军,1985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设计和执笔撰写了有关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等改革方案。1986.5–1988.4担任学校团委书记,1988.5当选团12届中央委员,团上海市委常委兼学校部部长。继而,我全职在体制内一干就是4年之多。 时间到了88年底,我觉得团市委机关工作实在太过枯燥,于是决定去国外读博。目标是无需托福(TOFEL)成绩的欧洲大学,给凡是有名气的教授都发了申请信。89年春,在急切等待中,我无比兴奋的收到了比利时列日大学Teyssie教授的录取通知。后经一番周折,89年5月中旬我终于拿到了比利时签证,并于6月13日乘飞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然后乘车来到毗邻德国Aachen(亚琛)的Liege(列日)。 图3. 曾与江老师合作过的Eastmond教授的学兄,Dr. Ed Schofield,和Eastmond教授的博士生、Ed的女儿,Dr. Paula Schofield 到列日大学报道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当初从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的Teyssie教授是一位带点傲气的欧洲绅士,学术上比我想象的厉害的多。在他的实验室,有正式编制的助理教授、副教授5人(列日大学一个实验室就一位正教授),博士生约35人,博士后约15人,还有10多名实验员。研究课题覆盖面特广,横跨高分子领域的化学、物理、工程、材料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方向,实验仪器和设备也特齐全,其规模和学术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上实力超强的实验室之一。 后来了解到,我能得到Teyssie的青睐,成为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全是因为他当时有一欧共体资助的大课题,与法国最大的化学公司Elf联合从事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开发。有钱,当然需要合适的人。而我寄去的简历上显示硕士做的是阴离子聚合,还有丙烯酸酯基团转移聚合(GTP)的经验。 说实话,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的简历上显示的自己的学术底子有几斤几两。在华理全职从政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几次GTP小实验;读硕2年半,我痴迷于社会活动,任学校首届研究生会学术部长兼校方组织的、一半多为在校学生参加的巨型社团总会会长,我80%的时间和精力要么在写、贴海报,办讲座,组建各式各样的俱乐部活动,要么到复旦、交大、华师大等校去找研究生会同仁联谊、交流。最后,为了按时完成硕士论文工作,我还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远离上海,来到地处河南洛阳的黎明化工研究院,才能静下心来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关键实验。 Teyssie教授是个董事长式的学者。第一次与我约谈30分钟,就着重说了二件事:1. 我被分在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项目组。项目组的三个研究方向[4]我可选其一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自己定,不要问他,到时给他个书面的计划就行;2. 我就读博士期间,他大概只能一对一见我三次,这次,大约一年半后,还有就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平时,可以与他书面交流(那时还没电子邮件)。 [4] 课题一,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络合引发体系;课题二,丙烯酸酯类单体阴离子聚合大分子工程;课题三,络合活性阴离子聚合活性种结构和活性聚合机理。在当时这三个课题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啊,Teyssie教授是这样!不过,后来细想想,也蛮开心,因为我历来就不太喜欢有人管着做事,而且还可选理论研究方向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其实,我升为项目组长后,我和Teyssie还是经常见面一对一谈话,这些都是后话。 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确定使用变温 (-78oC至+25oC)、多核(7Li,13C, 1H,36Cl)NMR(核磁共振)直接探测阴离子聚合活性种的结构,研究不同活性种之间转换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及它们与活性聚合机理和立体化学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用Teyssie教授的话说,这个方向“作为博士论文课题,是一个相当令人敬畏的挑战(a ra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 indeed for a Ph.D. thesis)”。 但,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从事NMR的研究,我需要非常频繁地使用变温变核NMR仪器。Teyssie拥有的那台NMR是一位助理教授负责管理和操作。这位助理教授整天叼着雪茄,喝着咖啡,完全是个躺平的比利时德裔“葛优”。听到我详细的研究计划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我告诉你,王先生,我不喜欢工作,更不喜欢为外国人工作。 可是,NMR和他的帮助对我来说太太重要了,心想必须拿下他。尝试了若干方法,即使请Teyssie出面协调,都未果。山穷水尽之时,我发现他有一特殊爱好,喜欢到世界各地收集矿石,但就缺一种含铁元素的,只在中国有。抓住这个机会,义松来列日时,我托他想方法弄来了二大盒几十块五颜六色的矿石(有那种含铁的)。作为礼物,我送给了这位助理教授,他一改历来严肃和不耐烦的态度,从此与我成了好朋友,后来还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不过,话说回来,刚做实验的几个星期里,一方面由于从大上海从政到小列日求学,心里落差很大;一方面由于业务生疏,自己特心虚忐忑,在同学和同事面前出尽了各种洋相。由于忘了灭掉煤气灯的火头二次,把实验室同一位同事的二条新的的确良裤子烧了几个洞;做环氧乙烷单体纯化时,玻璃反应烧瓶爆炸,快速转动的磁力搅拌子如子弹一样飞射而出,擦着我的脖子皮肉而过...... 中国人有三点很特别,不信邪,肯吃苦,学的快。几年中,几乎所有周末、假期我都非常享受地一人泡在实验室。“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到2个月,我慢慢进入状态,找回了自信和感觉;正式上班后不到5个月,我已用打字机打出了一篇论文,放在Teyssie教授的办公桌上,请他修改[5];读博的第3个年头,我被任命为丙烯酸酯类活性阴离子聚合项目组组长。项目组共7名成员,有实验员,硕士和博士生,还有博士后。我成了不拿助学金而拿工资的博士生。至今想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Teyssie真是个伯乐和大科学家,他居然如此放心,让我这个还是在读的学生领导和管理当时他实验室最大的项目组,在业务上去指导来自法国、土耳其的三位博士后。 成为项目组组长后,我是一边利用周末、假期独立完成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一边带领项目组成员与Elf合作进行络合引发体系和大分子工程的研究和开发。我天生特喜欢那样的多重任务(multi-tasking),也非常享受由此带来的成就感(fulfillment)。 得益于Teyssie的信任、苛刻甚至严酷的要求、指导和指引,我在他的世界顶级实验室跌打滚爬了五年,练就了终生受用的本领。从深刻理解聚合化学(尤其是活性聚合),到熟练的阴离子活性合成技术,均为日后发现ATRP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博士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开发的多核NMR技术也成为一种新的直接而有效的研究手段,后被同行学者广泛使用。93年11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大获成功(图4,图5),获得了评委祝贺最优博士学位(A+)。比利时大学博士学位分A+,A, B, C, D, E六个等级,其中A+是得到评委祝贺的最优博士学位,LA PLUS GRANDE DISTINCTION ET LES FELICITATIONS DU JURY (最优秀和评委祝贺) 。A+博士凤毛麟角。我毕业时,临近退休的Teyssie教授一生总共培养了70个博士,只有3位A+博士。据说,迄今为止,我是列日大学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唯一获得A+博士学位的。 源于五年的研究成果,我共发表了20篇文章(一作16篇),其中16篇发表在Macromolecules上(一作14篇),这些文章涉及到丙烯酸酯类络合阴离子活性聚合几乎所有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方向。项目组的横向合作也硕果累累,产生了12篇欧洲和美国授权专利,3个新的活性聚合络合剂,还有2个新的活性聚合产品。我一生真是非常感谢Teyssie教授,他充分信任和放手让当时还是小白的我独立进行博士论文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而且非常慷慨的给足科研经费,使我有了无忧的试错机会和宽松的创造空间,为丙烯酸酯类单体阴离子活性聚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开发做出了贡献。 图4. 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台上)宣布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我获得“评委祝贺最优博士学位”后,我非常激动,用不太正宗的中式法语说 “vous êtes très gentils du jury”(您们是非常绅士的评委),引起大家开怀大笑(仰天大笑的二位是我的二位导师Teyssie教授(右)和Jerome教授(左),迎面微笑的是我文中提到的那位NMR助理教授(只看到头),Jerome左边那位穿牛仔裤和咖啡色上装坐着的中国留学生是来自复旦大学的田东同学,他那年刚到列日大学Teyssie实验室读博。 图5. 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后举行的答谢招待会上,博士导师Philippe Teyssie教授和前来参加我论文答辩的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教育处陈参赞握手致意 [5]我在列日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Macromolecules, J.S.Wang,R.Jerome,R. Warin,and P.Teyssie, Anionic polymerization of acrylic monomers. 10. Carbon-13 and lithium-7 NMR studies on the monomeric model of living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Macromolecules 1993,26,6,1402–1406。这篇文章是NMR研究活性聚合机理系列中的第一篇基础文章。Teyssie把关非常严格,我花了2年多时间,修改了20多遍,直到他没有任何疑问,方发出发表。 随着丙烯酸酯类单体活性阴离子聚合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彻,我越来越感到活性阴离子聚合的局限,而且认定活性自由基聚合才是高分子学术研究和应用开发的未来。于是,从93年初起,我开始关注活性自由基聚合的研究动态,并准备博士毕业后去美国做博后研究。后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tyjaszewski教授(老马)和美国Akron大学的 Quirk 教授[6]都给我发来邀请,均是活性自由基聚合课题。Quirk教授还专门提及研究用fundamental approach(基本方法)控制活性自由基聚合(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去了Quirk实验室,我这30年的人生绝对是不一样的)。可惜的是,94年春天收到Quirk回信之前,我已于93年10月10日正式回信告诉老马,决定去他实验室,并约定94年5月开始工作。后来列日项目组的工作实在太多,需要一段时间交接,老马那边办理H-1签证也迟迟没下来,一直拖到94年9月1日,我才带着ATRP的原始设想,憧憬着加入老马团队,携刚出生的儿子,踌躇满志,登上飞往美国匹兹堡的飞机,开始ATRP新征程。 第一篇ATRP文章发表后(J. Am. Chem. Soc.1995,117, 20, 5614–5615.),我许多列日的同学同事怀疑我在列日读书工作时就已经悄悄在实验室动过手,做过类似实验。是的,我去美国前还是一个活性自由基聚合的素人,按常理,如何能在120天内,有这么大的发现?1995年在美国化学会春季年会期间,我约Teyssie教授品赏了一顿久违的法国菜。席间,谈到人们的议论,他说他信我,还说我可是他的实验室里出了名的“高产”和“金手、快手”博士毕业生。为了不想让导师遗憾,那次交谈时,我没告诉Teyssie一个也许他已知晓的秘密,最早期的ATRP的构思确确实实是在他实验室工作时形成的。 故事未完,请见续篇(题目暂定):“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2,列日的匹兹堡”和“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3,匹兹堡的列日”。 [6] R.Quirk教授是我硕士同门师妹任杰在Akron大学读博的导师,也是Teyssie的好友。Quirk是世界著名的阴离子聚合教授,与我硕士导师华理应圣康教授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应老师的硕士生都成了Quirk教授的博士生、研究助理。93年他来列日参加为Teyssie教授退休举行的学术会议期间,我请他和他的太太,还有也来列日参会的南加州大学Hogen-Esch教授、德国Mainz大学Muller教授等一起到我家品尝了一顿西式中餐。在列日,读到Quirk教授和任杰师妹发表的GTP机理的文章,点亮了我如何控制活性自由基聚合的灵感,这将在“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2,列日的匹兹堡”(暂定)中分享。 尾声 写好这篇文章初稿后,我发义松请他斧正。他发来了一张摄于2020年8月13日的照片。那天义松约我一起去浦东梧桐人家看望江老师和师母。相隔30年,饭后,我们又一起议论起大家关心的议题(图6)。有的是,列日缘份绵绵不断! 图6. 近30年后的2020年8月13日,在江老师家里,我们又一次在一起探讨大家关心的议题(右起于义松、王锦山、李文俊、江明、李夫人薛碚华)。江明和李文俊两位老师是同学,同事数十年的好朋友。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
技术支持:陈国颂-江明课题组 网页设计与维护:卞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