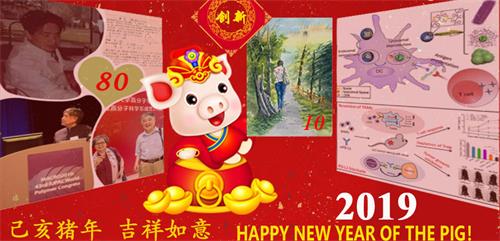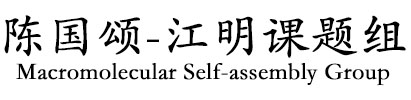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从北大到清华,从工人到教授——涂料泰斗洪啸吟的炫彩小故事 从北大到清华,从工人到教授——涂料泰斗洪啸吟的炫彩小故事
郭明雨
2023年12月12日,小编有幸于上海梧桐人家养老社区江明院士的家中(图1),采访了清华大学的洪啸吟教授。本期,请随小编一起聆听这位履历丰富,几近传奇的涂料泰斗的炫彩小故事。
图1. 左起:刘晓亚教授、冯汉保教授(洪教授夫人)、江明院士、洪啸吟教授和小编(2023.12.12摄于江明院士书房)
(洪:洪啸吟 教授 江:江明 院士)
小编:洪老师好!您在聚氯乙烯、彩色电影胶片、塑料钞票、光刻胶及光刻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在涂料界更是大名鼎鼎。很荣幸您百忙中抽时间接受我们《旦苑晨钟》的采访,与我们的读者分享您涂料泰斗的炫彩故事。 洪:涂料泰斗不敢当啊,我只是涂料界的票友,我的主业是光敏高分子化学。想听故事,我有很多,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
[1] 洪啸吟, 我与涂料的不解之缘——写在《涂料化学》第三版出版之际,科学出版社公众号,2019.07.05; 陈帅, 徐景坤, 申亮, 涂料泰斗洪啸吟讲述科学史,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20, (6), 1-5.
小编:太好了!那我就先问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您和江老师都是1938年出生,江老师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您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2),为什么晚了两年? 洪:哈哈哈,这个问题难度确实有点大啊。江老师是学霸,中小学跳级了吧? 江:不不不啊,我们那时候对上学年龄没有要求,我上学稍微早点,我在复旦大学1955级化学系的同学中也是年龄比较小的。 洪:还有一个原因,我曾因生病休学了一年,这样两年就对上了吧,哈哈。 图2. 洪啸吟(1958年摄于北京大学)
小编:我们还注意到您是1963年毕业的(图3),为什么是6年制?相当于现在的本硕连读吗? 洪:不是的。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行的是6年制本科,我们北大自称“太学”。我1963年毕业后,又经考试被录取为冯新德先生[2]的研究生(图4)。你看,江老师是1958年大学三年级就提前毕业了,这么一算我就落后他5年了,他2005年67岁入选中科院院士,我感觉5年后追上他有难度,所以2004年就退休了,哈哈哈。 图3. 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年级高分子班毕业留影 (后排左五:洪啸吟,二排左四:周培源 副校长,左五:陆平 校长。照片中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知名教授全部缺席,原因不详) 图4. 洪啸吟(右)与冯新德先生(左)
[2] 冯新德(1915-2005),高分子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我国高分子化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
小编:您1957-196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您伯父洪谦先生[3]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知名教授,你们叔侄之间经常有往来吧? 洪:几乎没有。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虽然他是知名的哲学教授,但我在北大的很多年里,从没提过他是我的伯父(图5),除冯新德先生等极少数人外,没人知道我是他的侄子,连我夫人也是多年后才知道的。 图5. 洪啸吟(左)与洪谦教授(右)
[3] 赵星宇,韩林合,洪谦:暗随流水到天涯,光明网-《光明日报》,2022.04.18.
小编:您1967年被分配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在工作期间曾偷偷翻译英文版 《高分子合成》丛书,能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吗? 洪:这个说来挺有意思。当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先是包装工,后改操作工,劳动之余,有时闲的无聊,就跟冯先生说想学点什么,他说那就学英语吧,给了我英语版《高分子合成》的前几卷,让我有空时翻译。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看英文书是危险的。恰逢其时,化工二厂的过氧化物引发剂车间需要操作工,因为过氧化物的生产过程很危险,容易爆炸,生产车间在一座孤立的防爆厂房内,工人都不愿靠近,更不愿意去那里劳动。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去,冠冕堂皇地说为了好好改造,愿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劳动。在那里我可以隔着防爆玻璃,一边观察危险的反应釜,一边看书做翻译。和我同组干活的还有两名老工人,他们很同情我这个臭老九,大家相处极好,为我保密。领导也从不来视察,一是因为危险,二是因为我曾为工厂解决过生产中的重要问题,颇有名气,对我较为信任,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即可。这就是所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完成了《高分子合成》八卷中前几卷的翻译,同时还写了一篇有关引发剂的综述论文。另外,当时我的英语水平不高,我们大学本科第一外语统一为俄语,第二外语我选学了德语,同时自学哑巴英语。上研究生才修了英语课。为此冯先生请了胡亚东先生(图6)[4](后几卷为贺溥[5]老师)为我做校对。
[4] 胡亚东(1927-2018),高分子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曾致力推动恢复中国化学会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中的合法地位和中国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的席位。 [5] 贺溥(1927-2020),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长期从事高分子科学研究工作。 (申泮文(1916-2017),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中岳(1925-2015),曾任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化学会理事;张希(1965-),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吉林大学现任校长;苏勉曾(1924-2019),无机化学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
小编:还有一件事,我们听说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曾多次不顾危险,帮助过很多蒙受不白之冤的化学界的老前辈? 洪:帮助谈不上,也说不上什么危险吧。因为我那时候在工厂工作,有工人阶级身份护身,活动比较自由。我想已经是工人了,还能怎么样?所以就经常到他们家里陪他们说说话,有时候会带个西瓜过去,也会帮他们买点菜等生活用品。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也帮不了他们什么,他们也不需要什么,能有人陪他们说说话,可能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精神慰藉吧。这些老先生、前辈后来都对我非常好,也帮助了我很多。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作为学生和晚辈能做、也应该做的,真的算不上什么。
小编:您1973年被调往北京市化工研究所,参加当时的国家重点任务,这个是秘密军工项目吗? 洪:不是。是参加当时两个“国家一号任务”之一的印染法彩色电影胶片的会战工作。经过努力,克服难关,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小编:听说您之后还曾受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邀请,参加新的光刻技术的研究工作? 洪:对。经过努力,我们当时(1980年)发明的无显影气相光刻技术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1微米左右[6],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那时候台积电还没成立呢。该项研究的源头创新性成果,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以及高分子和半导体界多位专家的重视,还得了奖,登了报纸呢。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光刻技术研发工作停滞了。
[6] 裴荣祥,洪啸吟,韩阶平,金维新,一种新颖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半导体学报,1980,1(2),162.
小编: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您一直在北大读书,是我国高分子化学家和教育家冯新德先生的研究生,后来长时间在北京化工局系统工作,是怎么结识我国高分子物理研究和教育的创始者和奠基人钱人元先生[7]的?钱先生(图7)又是因何推荐您到涂料界最负盛名的美国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DSU)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呢? 洪:这个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刚才说的我们做的光刻技术非常好嘛,所以就想请人帮我们做个鉴定。冯先生是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我们自然有把握请他参加鉴定。但如果能再请上钱先生,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界的两大领袖同时参加,那鉴定的结果就更有说服力了。可是那时候我虽然在工厂做的还很不错,但在学术界还没什么名气,所以真的是怀着非常忐忑紧张的心情,敲开了钱先生办公室的门,毛遂自荐。没想到的是,钱先生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表态,说“这么好的技术,我一定参加!”。事后才知道,在所有的鉴定人员中,钱先生给了最高的评价。我就这么结识了钱先生,也给钱先生留下了好印象。改革开放后,美国伊思曼柯达公司的威廉斯教授访华,钱先生陪同。钱先生知道威廉斯教授要做感光树脂方面的报告后,立马就想到了我,把我叫去并介绍给了威廉斯教授。之后,又与威廉斯教授一起推荐我到NDSU聚合物与涂料系著名的光化学专家柏巴斯(Peter P. Pappas)教授(图8)课题组做博士后研究。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前面说到了,我是读了冯新德先生的研究生的,但当时国内没有学位制,所以我是没有学位的,官方也没有说相当于什么学位。但是由于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工作比较出色,国外教授认定我相当于具有博士学位,所以就做了博士后研究员。1981-1985四年的NDSU访学经历,让我受益匪浅,结识了涂料界的多位世界级权威大家,开启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生涯。在这里也要再次特别感谢钱先生,先生作为科学大家的胸怀和格局,是我一直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图7. 洪啸吟(左)与钱人元先生(右) 图8. 洪啸吟(右二)与Peter P. Pappas(右一)和Frank Jones (左二,涂料学知名教授)等
[7] 江明,科学巨匠 后辈楷模,《旦苑晨钟》公众号,2023.12.05.
小编: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您曾经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委和科工局等部门担任过很多基金的评审、评议工作,能给我们谈谈当年我国科研人员的经费情况吗? 洪: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吧,我参加过很多部门的基金评审、评议工作,算是为大家服务吧。那时候我国的经济刚起步,国家要大力发展科技,但经济困难,科研人员的经费都异常紧张,竞争非常激烈。我奉行冯新德先生教导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八字方针,就是审核的时候要明确提出申请材料和申请者存在的不足之处,多挑刺,找毛病。但审批的时候,不能因为存在不足就不批经费,该给的、能给的尽量给。同时,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做得好的科研人员得到经费支持,我们曾多次想办法让两个人分享原本一个项目的经费,就是一分为二的策略,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算是尽己所能,为大家做了些合格的服务工作吧。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的采访已近尾声。这是小编第一次面对面与洪老师交流对谈,一开始的心慌忐忑,在洪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爽朗笑声中,很快便消失殆尽。老师的那种阳光、坦荡和开放的心态,既是一种师长、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一种源自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吧。访谈结束时,我们这一老一少都觉得意犹未尽,相约以后有机会再到老师家中,继续听他讲炫彩的科坛故事。
郭明雨 执笔,洪啸吟 审阅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