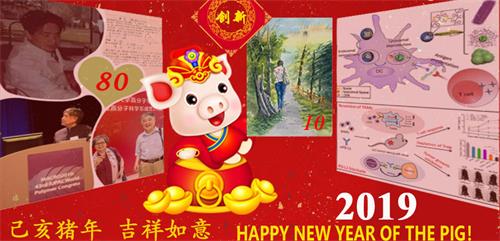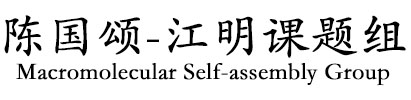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得遇良师,受教终生 :敬贺魏格纳教授84岁寿辰 得遇良师,受教终生 :敬贺魏格纳教授84岁寿辰
王健君
2001年从华东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受9.11事件影响,我去美国的留学签证被拒了。绝望中,我联系了当时在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做博士后的王朝晖师兄(现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因祸得福”,于2003年被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录取,前往攻读博士学位。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是世界顶级高分子研究机构,由6位著名教授轮流担任所长,每轮两年。我的合作导师是Wolfgang Knoll教授,他的团队是所里最大的,共有100多人。 图1. 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大楼(取自网络)
马普高分子研究所位于欧洲政教古都美因茨(Mainz),该市在欧洲国际河流莱茵河的西岸。据研究所的创所人Wegner(魏格纳)教授说,选在美因茨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是德国传统的化学研究中心,且交通方便,毗邻法兰克福机场。与国内众多高校、科研院所不同,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和马普化学所都在美因茨大学的校园里,当中没有围墙。美因茨大学的食堂也是开放共享的,所以“两所一校”的中国同学一般都会聚集在这里吃午饭,享受一天中最轻松愉快的“聚餐”时光。期间,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这里的大教授们,特别是大学的Ringsdorf(林斯托夫),马普高分子所的Wegner和Muellen(缪伦)三位。Ringsdorf教授是世界著名的高分子和超分子化学家,是大家最尊重的前辈。他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Staudinger(施陶丁格)教授的最后一位博士生,而我读博士时直接指导我的课题组长Ulrich Jonas教授(当时我们都称他为Uli),是Ringsdorf教授的最后一个博士生。记得2005年,Uli从中国出差回美因茨,与我说起张希老师是Ringsdorf教授的得意门生。所以这么算起来,我和张老师还算得上是同门师徒。施陶丁格这棵大树(国外称Academic Family Tree,国内叫科学族谱)枝叶繁茂,张老师是刚健的分枝,我应是一片嫩叶。 说起Muellen教授,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改论文非常快。据说他一般隔天就能把论文的修改建议返回,这是博士生们最关心的事情。导师改得快,学生当然开心。但太快了,原来完成初稿想休息两天的美梦就被击碎了,也会不适应。Muellen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很厉害。记得他的一个学生曾提到:有一次Muellen教授在走廊里碰到他,问他工作怎么样了。他简单地回了句“还可以。”结果教授竟然勃然大怒,把那个学生教训了一通。估计教授原本期望那个学生能给他详细地汇报一下研究进展的。去年9月,Muellen教授曾经的博士后,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高端化工与能源材料研究中心的主任智林杰教授举办了一个会议,我也去了。晚宴时Muellen教授告诉我,他培养了70多位中国教授。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马普所的Wegner教授也是大家谈论的热点。他是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的两位创所人之一,另一位是高分子物理奠基人之一的Fischer教授。Wegner教授早在1969年就首次报道了二乙炔的拓扑聚合[1],但却没有研究其导电性。2000年4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Ober教授在Science上发文,专门介绍了Wegner教授在高分子领域的贡献[2]。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A MacDiarmid,A Heeger及H Shirakawa三人,基于他们1977年在聚乙炔等导电高分子方面的贡献。这样,Wegner教授也算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虽然从未听他自己这么说过,我们学生还是会为他扼腕叹息。大家都十分赞赏Wenger教授的学术领导和外交能力。他在1996-2002年期间就担任了德国马普协会副主席,主导了协会与中国科学院,乃至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很多学术合作。他发起了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的合作。很多知名的中国学者都曾是这些计划的受益人。 图2. Wegner教授近照
Wegner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让我十分仰慕。所以在读博士的后期,我就有了到他那里做博后的想法。另一个原因是,我钦佩他的为人。我在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碰到过他几次,我相信那时他并不认识我,但总是微笑相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进所,他还为我开了门,并示意让我先进。感觉他真是和蔼可亲,是一位“绅士派学者”。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就将我的简历发给了Wegner教授。可能是他太忙,邮件发出后一周,我没有收到回复。当时我很着急,犹豫再三后,在发给他邮件后的第二个周五的下午,我拨通他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竟然就是Wegner教授本人。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Wegner教授直接回答说,看了我的简历,欢迎我博士答辩结束后到他研究团队去开展博士后研究。 2006 年10 月我加入Wegner 教授研究团队做博士后。按照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的惯例,我需要先做一个学术报告,介绍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及未来的工作设想。报告做完后,Wegner 教授来到我面前,说我的报告非常精彩。我很是诚惶诚恐,赶紧说:“以后多多向您学习。”接下来Wegner教授的话,令我非常吃惊,他说:“以后我们互相学习。”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Wegner教授的学术地位是非常高的,而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前几年,现任吉林大学校长张希教授曾做过一个报告,题目为:我向谁学习?介绍了他从他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研究进展。我想大概有大学问的科学家都是很谦虚的。 我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高分子调控生物矿化。Wegner教授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还让我指导一个中国的硕士留学生开展这项研究。2007 年 5 月,Wegner教授进一步要我负责一个工业项目,并将我提拔为课题组长(图3,4)。这样我就有更多机会向他请教了,我基本每周五下午都会去找他。教授的办公室分三间,第一间坐着他的秘书;中间的大间是他平时会客、处理日常事务用的;最里间是他平时看书学习的地方。周五我找他请教、与他讨论时,一般都是在最里间,我感到特别亲切。有一次,我敲门进到里间时,看到他拿着一本微流控方面的专业书,边看边做着笔记,那时他已将近70岁了。想起日常讨论时,他经常能从满满的书架上信手抽出某一本,告诉我那本书的第几章有我感兴趣的知识,这使我惊叹不已!这我相信那满书架上的书他是全部看过的。虽然我回国已经快15年了,Wegner教授读书做笔记,孜孜不倦学习新知识的画面,犹在眼前,也激励我坚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回国前夕,我向Wegner教授请教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后如何选题的问题。教授回答道:“未来的研究方向你自己决定。但是不管以后你开展什么研究方向,合作非常关键,因为在现今社会上仅靠一个人把事情做好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我有点迷茫,他继续道:“一个好的研究方向刚开始时应该是像小溪,几乎没有声音,关注的人很少;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该研究方向会成为大江大海。”他边说边用右手模拟溪水缓缓地流淌的样子。并补充说:“很多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刚开始时都是非主流的,不受人关注的,比如Staudinger教授。”他的这些说法看似平常,却使我受用一生。 图3. 2006年圣诞节假期Wegner教授夫妇(右排中间和左排中间)请我(左一)和我妻子(右三)及一对土耳其博士后夫妇(现为土耳其教授)在美因茨的一家泰餐馆就餐
图4. 2009年4月在瑞士巴塞尔与企业合作者研讨结束后在莱茵河的桥上拍照留念
2010 年 2 月,我博士后研究工作到期,Wegner 教授为我写了足足两页的推荐信,推荐我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2008年南方大雪灾震动了全国。我想我们也应该为解决这个难题做点贡献,于是我毅然选择了冰晶的形成机制与应用做为我的研究方向,后来又自然地拓展到了细胞、组织甚至器官的控冰保活和冻存这个生命相关的领域(图5)。2010年工作启动初期,国内防冰研究非常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系统的表征和评估材料防冰控冰性能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建立评估材料表面与冰粘附强度的平台作为首要的任务。得益于博士后期间我随Wegner教授开展的高分子调控生物矿化研究的经历,我们先后建立了研究材料表面对冰晶成核和生长影响的可靠评估方法。这些方法的建立难度大,耗时长。我和三个博士研究生一起,用了大概四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这期间我的科研“产出”非常少,几乎没有研究论文发表,这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是很罕见的。幸运的是所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对我表达了理解,并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我个人内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有点失落。 图5. 冰晶形成机制研究的两个重大应用出口
我虽然早已离开马普高分子所,但Wegner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从未停止。2012年我向教授汇报工作时,他可能察觉到我情绪有点低落,就鼓励我说:“你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我刚开始研究时选的方向有点像,关注的人不多,起步难度大,但很有新颖性,应该坚持下去。”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出乎我的意料,他在2013 年 3 月又正式邀请我去德国访问,并安排我去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弗莱堡大学和莱布尼茨研究所等 7个德国高校与研究所,与开展类似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并做报告。每场报告结束后,均安排了大约半天的时间让我与当地的教授、博士后和博士们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讨论。这次德国访问交流大大加深了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的理解,也结识了一些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我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 图6. 2023年10月25日我(右一)在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交流结束后,与Wegner教授夫妇(分别为左一和左三)合照;左二为我的妻子;右三为我的博士生刘杰,现为中科院化学所的研究员;右二为马普高分子所的Butt教授,也是刘杰在德国开展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
回国后,大受启发与鼓舞的我,开始利用Wegner教授当初告知的研究方向可以自己选,但一定要多合作交流的思想,与中科院化学所、北京大学、中科院大学、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美国Nebraska Lincoln大学的前辈、同事和朋友展开广泛合作和深入交流,大大推动了我的研究,终于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3-4],包括在Nature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上研究成果。 Wegner教授是我十几年前博士后时期的导师,但回顾起来,他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从未停止。在多年的相处中,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去年10月,我和夫人及我的学生特地去教授Mainz的家中看望了老师和师母(图6)。今年1月3日是老师的84岁 寿辰。我借《旦苑晨钟》平台发布此文,祝贺敬爱的老师Wegner教授和师母健康长寿,青春永驻!
参考文献 [1] Wegner, G., Naturforsch. Teil B 1969, 24, 824-832. [2] Ober, C. K., Shape persistence of synthetic polymers. Science 2000, 288, 448-449. [3] Bai, G.; Gao, D.; Liu, Z.; Zhou, X.; Wang, J., Probing the critical nucleus size for ice formation with graphene oxide nanosheets. Nature 2019, 576, 437-441. [4] Xue, H.; Li, L.; Wang, Y.; Lu, Y.; Cui, K.; He, Z.; Bai, G.; Liu, J.; Zhou, X.; Wang, J., Probing the critical nucleus size in tetrahydrofuran clathrate hydrate formation using surface-anchored nanoparticles. Nat. Commun. 2024, DOI:10.1038/s41467-023-44378-6.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