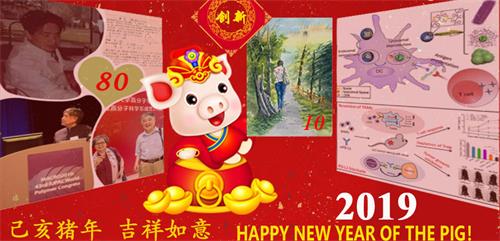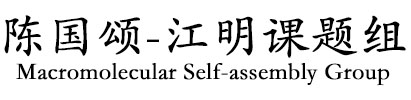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人生前路有光,凡事以微见长 人生前路有光,凡事以微见长
赵宇亮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中原弘道先生
江明先生创建公众号《旦苑晨钟》:讲科学背后的故事,探故事背后的科学,记叙学界楷模,增强科学情怀。立意高远,所以,江先生约我写一篇短文,我欣然答应。但当我品读了前面几篇创作以后,发现《旦苑晨钟》记叙的微故事,犹如科学思想的传承介质,是滋润后学的营养液。于是我便犹豫再三,因为我自己也是需要不断提高的后学一辈。今日晨跑,30-40年前求学、工作时的一些往事片段跃然眼前,记之以谢江先生的邀约之情,同时也献给我尊敬的导师中原弘道先生[1](图1)。
图1. 赵宇亮与中原先生(右)共进晚餐(2000年,东京新宿)
[1] 中原弘道(Hiromichi Nakahara,1936-2021),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日本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创始人。一生从事原子核反应和超重元素研究,对日本乃至国际核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5年四川大学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交通靠走,治安靠狗,通信靠吼,助兴靠酒的大山沟里工作。为了消磨工作之余的无趣时光,我又捡起了小时候的文学梦,开始了诗歌甚至小说创作,曾经一度沉浸其中,自得其乐。直到有一天,研究室主任让我为全室职工讲一堂内容自定的化学课。本想偷懒,觉得元素周期表好讲的我,没想到把自己给“绕”进去了。为了备好课,不得不到图书馆去查资料。结果不查不知道,看似简单的元素周期表,我在每一个元素的背后看到了一套庞大的化学、物理知识及其系统的规律性。由此也激发了我对科学探索和研究的兴趣和动力,于是开始把时间和精力用到科学实验上。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做实验,自告奋勇承担实验区晚值班的任务,名正言顺地住进了值班室。一住就是三年,在不知不觉中,科学研究已成了人生的爱好和生活习惯,把曾经的文学梦抛到了九霄云外。 得益于那段时间的努力,我于1989 年获得了赴日本原子力研究所交流学习的机会,随后又考入东京都立大学中原弘道教授的研究室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从事核燃料裂变碎片质量测量分析和原子核裂变路径的研究工作。核裂变现象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Otto Hahn)和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在用慢中子轰击铀-235时发现的,因为测量到了铯-137和锶-90等元素,这些元素的存在表明铀-235原子核已经被分裂成更小的核碎片。原子核裂变的发现,不仅成为制造原子弹等核武器的科学基础,也因此开创了核物理学的新时代。人类得感谢这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因为我们现有的大多数高精尖技术,都跟20世纪核物理学研究和核技术的发展有关。这个话题,此不详述,留给有兴趣的读者去研究。 记得刚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毕业,中原先生笑着对我说:我培养了30 多个博士生,按时获得学位而没有延期的只有三人,你可以争取成为第四人。只要你做出一件以前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工作就可以毕业了。后来,为了能按时毕业,我又开始了当年山沟里的生活习惯,经常在实验室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回家,最长曾经3周吃睡都在实验室。 刚开始进入实验室时,因为涉及放射性实验,有很多非常严格的实验室要求和规矩,否则就容易造成“放射性事故”,所以中原先生指派了一位师兄A带我做实验。这位A师兄教我做实验很积极,天天来指导我如何使用各种仪器设备。有A师兄热心帮助,我天天高兴也很感激。但是等情况熟悉了,我发现了问题,博士学位一般是三年,A师兄在实验室已经是第六年了,他自己一直没有毕业,也没有着急要毕业的样子,天天来帮我,这是为什么?这个疑问在我脑海里久挥不去。一晃就一年过去了。 中原先生有个习惯,经常下午3~4点到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每周3~4天)。他每次都带一个学生去,他出钱请学生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学生自己的或别人文献的最新科研工作进展,那时候还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PPT,被叫到的学生就匆匆忙忙拿上几张实验图或者实验数据纸或者实验笔记本,坐上中原先生自己开的车,从校园下山,直奔学校附近那个最贵的咖啡馆。我问过同学,为什么总去最贵的那个咖啡馆?同学淡淡的说,“大学教授,是有身份的呢”。 轮到我享受学术咖啡时,已经是我入校快两年了。那天下午,中原先生跟我讨论了美国理论核物理学家提出的“原子核多路径裂变假设”,讨论我们能否设计实验去验证这个理论假设?一边讨论我一边在纸上画,这成为我人生第一篇科研论文的源头(后来发表在PRL)。这次讨论持续到了晚上7点左右,又一起晚餐,还是中原先生掏钱请客。晚餐中,可能是思考累了,中原先生换了话题,再也不提科研实验的事,只是杂谈。于是,我就借机问了那个让我好奇的问题:“为什么A师兄七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无私指导我做实验?”中原先生好奇地看着我,笑了笑,他说:“我的职业是教授,把学生培养合格再交给社会,是我的责任。A君实验能力很强,但是科学水平没达到博士学位要求。他又很想从事科学研究,只要他愿意坚持到底,我就给他机会,人生的价值多半是由长度和厚度决定的,多花几年有什么要紧,等他科学的Sense开窍了,就好了。” 事情看似微小,恰恰在小事中,体现的是教育家思想的闪闪发光! A君的实验技能以及对科学研究持之以恒的淡定,在随后我们与RIKEN(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团队十年合作共同发现113号新元素Nh(鿭)(图2),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2. 2017 年,我(右二)和中原先生(中)应邀在东京出席113 号新元素命名庆典。Nh是113 号元素的元素符号(英文名Nihonium的缩写)
1999年我成为中原先生的第四位按时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后,继续在RIKEN从事核反应合成超重元素的研究。2001年回国,因为缺乏从事核反应实验研究所需要的加速器等实验设施,也是受中原先生的“做一件别人以前没有做过的研究工作”的影响,我跨学科转行到了纳米科学领域,从事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完全离开了在国外的核物理研究领域。 2001年9 月,我提出了“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的概念,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图3),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展该领域研究的3个国家之一,形成了学术界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纳米安全性或叫纳米毒理学。2005 年12 月我应邀领衔美英德日等11个国家科学家撰写纳米毒理学领域的世界第一本教科书《Nanotoxicology》(图4),2007年初在美国出版后,多次重印。一位美国教授当时评价道:在一个新出现的科学研究方向,由中国学者领衔撰写世界上第一本教科书,这在2005 年前还很少见。
图3. 赵宇亮与中原先生(右)在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2006年)
图4. 赵宇亮与中原先生(左)在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2006年)
一路走来,很多人问过我当时“怎么能转行跨这么大的学科?”我想,这可能得益于中原先生给予的卓越的科学研究方法学的训练。一个受过正规而系统科学研究训练的博士学位持有者,应该具备充分的能力去从事任何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 中原先生一生从事原子核反应和超重元素研究,对日本乃至国际核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多次到中国来访问讲学(图5)。不幸的是,先生于2021年染新冠去世。谨以此文再次表达学生对先生的敬意和悼唁。
图5. 赵宇亮与中原先生(左)在香山科学会议晚宴(2008年,北京香山)
赵宇亮,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主任。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1996和1999年分别获得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之前在国外从事原子核反应动力学和超重元素研究,和RIKEN(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同事一起发现了113号新元素Nh(鿭),是元素周期表中亚洲国家发现的唯一新元素。2001年回国,率先开始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是纳米毒理学领域的开拓者。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