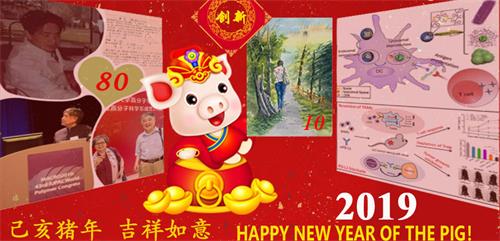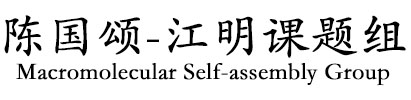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探寻英国建筑师雷士德 探寻英国建筑师雷士德
潘一婷
1. 被找到的“Lester Girl” 2023年12月20日我的苏大邮箱收到一封特别的邮件,来信人是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郭明雨教授,他偶然发现我曾先后两次在英国获得雷士德基金会(Henry Lester Trust)的资助,并告诉我他的博士导师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的江明院士1988年也曾受该基金的资助赴英国访学。Shanghai Daily(上海日报)的主任记者、研究建筑史的乔争月老师和江院士正在联系寻找更多获得该基金资助的中国人,期盼进一步研究、了解关于Henry Lester先生及该基金会的故事。而我正是那位他们找到的第一位新一代“雷士德女孩(Lester Girl)”。 通过郭老师的引荐,我有幸和前辈江明院士取得了联系。他亲切地跟我分享了他是如何通过同济大学的华霞虹教授[1]和乔争月老师在上海养老社区的讲座,偶然重新“发现”雷士德基金会以及自己正是受助人的惊喜,并告诉我寻找更多雷士德基金会的中国受助人是他近期十分关心的事,而他的学生郭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他,找到了Lester Girl,找到第一位LG是一个重大进展。
[1] 华霞虹,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时代建筑》兼职编辑,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学术顾问。
江院士的话立即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2年前在英国留学的自己,当时我是剑桥大学建筑与艺术史学院建筑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研究内容是从建造史的视角研究上海的本土传统和英国影响。虽然我读博士的第二至第四年均获得了中国留学基金委(CSC)的奖学金资助,但是在读博士的第一年,由于留学基金委尚未开通海外申请通道,我便申请其它渠道的奖学金来作为补贴。 在我得知英国的Henry Lester Trust提供奖学金,并且要求受助者条件是“中国公民”、“在英国大学或机构进行学习研究”、“优先考虑医学、健康相关课题,以及建筑学领域(包括规划、建造管理等)”时,我感到欣喜之余,心中也有些诧异。是什么样的外国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人,并专门强调研究方向包括建筑学领域?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基金会背后的慈善家正是上海20世纪初德和洋行的创始人、英国建筑师亨利·雷士德(1840-1926),而外滩的多座建筑都是出自德和洋行的设计。 图1. 我(左一)参加剑桥大学博士导师James Campbell教授(左三)办公室里的研究生研讨会一瞥(Dr Karey Draper摄于2015年) 图2. 我和博士导师Campbell教授(右一)一起走向剑桥老参议院大楼参加博士学位授予典礼(2016年)
在给雷士德基金会邮寄了经费使用计划的申请书之后,我很快就收到了基金会的确认函。基金会后来将奖学金支票寄给了我所在的建筑系,经由我的博士导师James Campbell教授(图1和图2)转交给我。在CSC奖学金结束后,我读博最后半年的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再一次有幸获得雷士德基金会资助。前后两笔奖学金共计5000英镑。我将它们用于回国田野调查、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图3和图4)、生活补贴、以及毕业阶段论文打印等费用。 图3. 2014年在博士导师Campbell教授带领下协助组织了第一届在剑桥皇后学院举办的建造史学会会议,照片为会议最后一天的Formal Hall 图4. 我在2015年英国建造史学会会议上做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报告
2012年,我有幸收到邮件邀请,参加雷士德基金会为当年所有受资助人举办的鸡尾酒会,地点就在伦敦的香港太古集团大楼里(图5)。作为学生,我平日在剑桥的日常是比较朴素的,但那天下午我特意翻出衣柜里的一条旗袍裙子,以表达我对聚会和基金会的重视,坐火车从剑桥赶到伦敦。当天我遇到了不少从牛津、纽卡斯尔等英国从南到北不同大学专程赶来的那年雷士德基金会的受资助者,全都是中国学生,大家举着酒杯,畅谈各自专业学习中的见闻。“Henry Lester”本人也是那个难忘时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讨论着从不同来源获得的对他的了解。当时我申请奖学金的通信联系人是太古集团的James Adams先生,在酒会上也遇见了这位老先生。虽然至今不了解基金会和太古集团的具体关系,但当天聚会上看到操持基金会的都是几位很年长的英国老绅士,对到场的学生们都非常和蔼,不由心生敬意。 图5. 2012年4月16日我收到的雷士德基金会受资助人聚会的邀请邮件
尽管并非在场的每个人都完全了解身为建筑师的亨利·雷士德在上海近代建筑业中的卓越贡献,但我默默地观察到,在这群值得雷士德信任的英国下一代绅士和更年轻的中国未来学者中,雷士德所希望传达和传承的一些价值观,在他们的交谈中和洋溢笑容的脸上闪烁着生机。在随后的漫长时光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价值观可能是一种超越文化的友善,也可能是一种跨越学科的视野,还有可能是一种来自心底深处的社会责任感。
2.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关于雷士德,熊月之先生曾在房芸芳著的雷士德传 “大爱无言”的序言中提到:“雷士德从什么时候萌发了捐献全部财产的念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类似雷士德的人还有没有?雷士德留给人们思考的空间、研究的空间都很大。”[2]
[2] 熊月之,“序二:大爱无言”,pp.1-3,房芸芳(编著),遗产与记忆—雷士德、雷士德工学院和她的学生们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其实雷士德基金会的资助并不是我第一次收到的由建筑师捐赠的奖学金。早在2004-2008年期间,我还在同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当时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里就传出一个轰动的新闻:常青教授(图6)[3]主持的研究室获得了首届Holcim国际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亚太地区金奖,但他决定把所获奖金几十万元捐赠出来,设立了“风土保护奖学金”,鼓励建筑遗产保护专业的优秀学生。常老师在2003年创建了中国首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后来因为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突出成就,于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我就是这个新专业的第二届学生。因为当时本科期间学习比较用功,我有幸先后三次受到“风土保护奖学金”的资助。我在大四取得了校内保送资格,幸运地被常老师收于其门下。在学院选派第一批保送生去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深造前,我在常老师教研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
[3] 常青(1957- ),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会士(Hon. FAIA)。现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城乡历史环境再生研究中心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常青专家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建筑遗产》学刊和《Built Heritage》英文刊主编。曾长期担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2003-2014)。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无论雷士德先生,还是我本科专业的创立者和引路人常青院士,我今天思索,他们都是建筑师,这或许并非偶然。“建筑师”历来被人们想象成一个社会改变者的角色。建筑师独特的培训模式,赋予了他们工程科学的严肃性和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对社会产生影响,并使公众从中广泛受益。当上天给予了某些建筑师超出常人的才华,以及随之而来的驾驭社会资源的机缘时,他们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奉献给社会,去推动一些对社会有益、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专业、学科领域的发展。雷士德虽然身为建筑师,但他跨学科的眼界,促使他除了大力发展英国工学院式的建筑工程师培养,还捐赠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和雷士德工程研究院。 图6. 常青院士在2023年6月17日的《开讲啦》节目中与广大青年分享他眼中的“建筑与风土”(图片来自网络)。节目链接:https://tv.cctv.com/2023/06/17/VIDEbCgnKeWsaWx2ZPESqYBq230617.shtml?srcfrom=sogou_vm
此外,雷士德将所有遗产捐献给上海的决定之所以“惊世骇俗”,除了社会责任心,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是一位英国人。跨越国界、对另一种文化的民众关怀爱护,并非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视野和胸怀。 实际上,这种社会责任心、跨学科的眼界、以及科研无国界的理念,我在剑桥求学时的老师们身上也看到不少。 我的博士导师James Campbell教授对世界的建筑历史充满了兴趣。他的著作《砖:一部世界史》(2003)和《图书馆:一部世界史》(2013)都以全球视角取径,并都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他正在写作的有关水利基础设施的建造与文明的新书,也是同他的合作建筑摄影师Will Pryce先生一起,到世界各地实地调研。他很敬仰也经常跟我和同学们提起的一位剑桥前辈学者 ,是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李约瑟和他所带领的不同领域科学家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为我国的近代建造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Campbell教授的社会责任心,还体现在他经常出现在许多英国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包括《Divine Designs》(第 5 频道)、《Modern Marvels》(历史频道)、《Making History》(Radio 4)、《Ancient Megastructures》(国家地理频道)、《Today Program》(Radio 4)、《Robert Elms》 节目(伦敦广播电台)、The One Show(BBC 1)和Excess Baggage(Radio 4)。他为《The Essay》(Radio 3)撰写的有关罗伯特·胡克建筑的节目曾在《本周精选》(Pick of the Week)(Radio 4)中得到专题报道。这可能源于Campbell教授讲课特别有意思,英国式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与此同时分析问题尖锐透彻。他通过这些媒体平台,不仅向公众普及建筑历史的知识,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学术之外为社会作贡献。Campbell教授的幽默感也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我记得在我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写完后的一次课题组会汇报中,开场白说:“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就好像生了一个孩子。这个过程的艰辛和困难,我这里就不提了,我现在就直入主题:给你们看看这个‘孩子’。”Campbell教授和其他同学都笑了。 另一位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汉学家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图7)。在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长Moffett先生和他的美籍华裔博士生Kang Tchou的引荐下,我有幸和方德万教授有过一小时的面谈请教。他对我曾经调研过芜湖很感兴趣,因为芜湖是李鸿章的故乡。他问我正在做的研究是什么,他如何可以帮助我。我当时关心近代建筑材料的运输,他于是建议我去调查海关档案,认为那里应该会有这些历史记录。之后,他问了我一些他关心的问题,包括上海的地势和沉降、水的供应、卫生排污设施、以及建筑的所有权等问题。与此同时,他用他自己熟悉的英国和欧洲的例子,解释为什么他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之后他又问我今年的计划,是否将回中国做田野调查。方德万教授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引导我的研究注意力,启发我思考。他提到的那些问题都很有洞见,都是建造史领域中与社会民生相关的深刻问题,不容易回答,但从长远看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图7. 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Campbell教授和方德万教授都很繁忙,都有很多学术任职和在指导的学生,但他们一直在坚持进行自己独立的研究。这一做法有助于使他们对一线研究保持高度敏锐和学术写作的熟练。有趣的是,虽然听说很难约到方德万教授,但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东亚藏书室,却极有可能“偶遇”到他。事实上我在那儿遇见他两次,因为他经常为自己的研究而亲自查找资料。 将雷士德的生活方式与此联系起来,雷士德过着极简朴的生活,长期居住在英侨总会的单身宿舍。他上下班时坚持搭乘电车或徒步,这或许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虽然我们无法直接了解他的内心感受,但可以推测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耶稣会修士一样不追求物质生活的理念。通过这种生活方式,他同时也更能深入理解当时的上海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或许与我在剑桥的导师们一直坚持进行一线研究的心态相似,都表现出对社会、生活和研究的敏感性。
3. 结语 “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雷士德基金会的受助人。你是否愿意分享你的故事?” 江明院士亲切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中。 “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江明院士带领学生们创建的“旦苑晨钟”公众号,致力于探索科学精神,造福成长中的年轻一代,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是情怀。这何尝不是社会责任心的美好体现。 其实不仅是在江院士和郭老师联系到我的当下,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当我回顾雷士德临终前的选择,心弦都会再次被触动。由于我的研究聚焦于建造史,我曾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探讨了建筑工具的近代转型[4],另一篇则研究了英国工学院运动对上海建筑业的影响[5],都从建造方法科学普及的角度尝试探讨雷士德工学院的贡献。这可以说是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尝试理解和纪念英国建筑师雷士德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史和遗产保护方向的学生,雷士德本是我研究上海建筑时,在故纸堆中搜索的研究对象,但他却跨越百年,在现实中为我提供了一笔研究资助,这种跨越历史时空的连接是多么奇妙啊! 我的书架上静静地伫立着一本由房芸芳老师2007年编写出版的《遗产与记忆—雷士德、雷士德工学院和她的学生们》,这本书随着我几年前迁居到加拿大。有时,当我翻阅其中,读到学生们对雷士德工学院充满深情回忆的部分时,我也很多感慨:当年的雷士德男孩们现在过得如何?其他受过雷士德资助的中国学生又身在何处?我真诚期盼更多的雷士德Boy和雷士德Girl能被江明院士找到,让我们一起看到这位曾经被遗忘的20世纪初在华英国建筑师、以及他所掀起和代表的一股力量在时光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4] Yiting Pan, James W.P. Campbell, A Study of Western Influence on Chinese Building Tools in Chinese Treaty Por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18, 17 (2), 183-190. [5] Yiting Pan, James W.P. Campbell, Mitchell's Building Construction goes to China: the impact of British Polytechnics, construction teaching, and construction textbooks in Shanghai (1870-1937),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3, 22 (2), 155-174.
潘一婷,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研究员,英国建造史学会(Construction History Society)理事会理事,建造史学会会刊《Construction History》编委。英国剑桥大学建筑与艺术史学院博士,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硕士,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学士,常青院士所设立的国内首个建筑遗产保护专业第二届本科毕业生。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