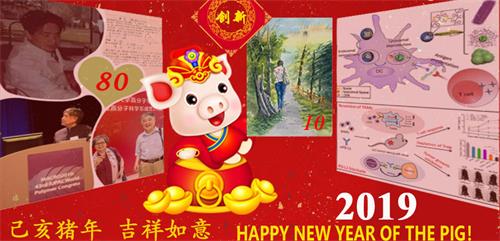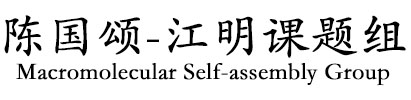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学术界还是工业界?——我的一家之言 学术界还是工业界?——我的一家之言
匡 敏
江老师倡导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呱呱落地两月有余,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甚至掀起了一股怀旧热潮,不少前辈学者通过自身的经历,讲述科学背后的故事,令人莞尔而动容。前段时间我和我先生段宏伟[1]携双胞胎儿子(图1)拜访江老师和师母,期间江老师说,《旦苑晨钟》的大部分文章讲述的都是学术界的轶事,鲜少文章提到工业界,希望我能写一篇介绍工业界经历的文章。恩师约稿,不敢不应。因此,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美国工业界的经历,希望对一些读者,尤其是还在纠结选择学术界还是工业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有所启发。 图1. 我先生段宏伟(左一)、我(左二)和我们的双胞胎儿子与江老师(中)合影
[1] 段宏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学士、硕士(导师江明院士),德国马普所胶体与界面研究所博士。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聚合物和无机纳米晶杂化材料、生物成像、药物释放、生物传感和催化等方面。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发布的《美国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ED)统计,2021年,打算进入商业或者工业领域的博士生(54.1%)是打算致力于学术界的博士生(26.9%)的两倍多 。工业界真的比学术界香吗?博士毕业后又做了博士后,最后转入工业界的我,也经历过这个“质疑—理解—成为”的过程。这种态度的转变,源自我在美国公司从事研发的经历。 我先后在初创纳米材料公司,医疗设备公司和特种化学品公司工作过,它们在各自领域都非常有代表性。初创纳米材料公司的主要客户是研究机构和研发实验室,产品不易放大生产,研发和生产没有明显的界线;医疗设备公司当时在开发一种与主营产品完全不同的新材料,有庞大的研发团队和中试车间(异地);特种化学公司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和其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研发规模小而精,不但有中试车间(in house),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异地)。 其中第二家公司是美国工业研发实验室的一个典型缩影,在那工作的几年对我个人的成长和职业规划都有深远的影响。固然,美国的国情和文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它的很多做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反思。 2010年以后,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从而推动了对柔性触摸屏的强劲需求,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医用胶片和显影仪器巨头Carestream(锐柯)成立了先进材料研究部(图2和图3),旨在开发一种可以替代当时主流ITO(一种透明导电氧化物膜)触摸屏的柔性触摸屏(图4)。因为在半导体量子点(蹭一下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热度)、金属纳米材料方面的研究经历以及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的研究背景与中心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我于2013年加入该公司,参与到FLEXX柔性导电膜的开发中。 图2. 2016年6月23日搬离明州时留念 图3. 2021年7月24日故地重游,叹物是人非 图4. 2015年4月23日公司家庭日,小朋友体验触摸屏
甫一入职,我就被研发部的豪华阵容震撼了。团队60多个员工中有三分之一具有博士学位。包括七八位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名校的毕业生。这些人当中有在3M工作了20多年的三朝元老,也有前州立大学教授,还有前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这样的人员组成加上自3M以来的研发秉承,奠定了FLEXX研发部的非凡学术气质。 浓厚的学术风格体现在团队内部不同的技术路线在技术总负责人的统领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上。当时,研发部不光在配方研发方面分成了两派,在涂装方式上也产生了两派。每个派别都希望自己的技术方案胜出,所以大家都是在明里暗里地较劲竞争。然而,在各个独立小组的例行技术周会上,主管都会鼓励和邀请其它各部门的技术大佬和小组成员参加。大家也不客气,既一针见血地给出思路和建议,又劈头盖脸地提出批评和质疑。我最早参加这些会议时,时而有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顿悟,时而又有惊涛骇浪剑拔弩张的恐慌,错乱到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一掐胳膊,真疼! 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也让FLEXX的开发实现了合成、配方、涂布、刻蚀、组装、专利(有自己的专利律师)和市场的全闭环。跨组、跨部门的合作频繁而紧密。我们应用小组的技术主管以前是军火枪械的结构工程师,触摸屏这种设计于他而言大概就是小儿科。每次我有问题去找他,他都是一副看弱智儿童的表情,一脸悲悯。 同时,研发部门与大学紧密合作。例如,公司的纳米材料开发组与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定期开会交流,从而保证了我们在超细超长纳米银线工业化制备的领先地位。 在产品开发上,公司强调研发一定要配合生产。研发的终极目标是求新求变,生产的终极目标是稳定易控。实现这两者的统一,其实是件很拧巴的事情。很多时候,实验室结果完美到让人恨不得马上去对手家踢馆,但是一上生产线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前一秒还是卖家秀,后一秒就惨变买家秀。让你痛苦到怀疑人生。我们每次中试和放大生产都是在三千多公里外的White City,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人口不足一万。但是,它的东北方向一小时车程,就是大名鼎鼎的Crater Lake,美国火山口湖国家公园(图5)!我去过两次White City,却从来没有去过Crater Lake,因为每次在那的两三天时间都是跟工程师在现场调试参数,有时甚至加班到半夜,根本无心看风景。做完放大生产后,试样又被马不停蹄地送回实验室进行评估,为下次生产提出指导意见。研发和生产之间就是这样不断反馈,相互磨合。多数情况下,生产能做的改变有限,这就对研发的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5. 离White City生产工厂不远处是McLoughlin 休眠火山
在人才培养上,公司提供技术型和管理型两种职业路径,并从各方面入手,为员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其中,让我受益最深的就是导师制。 导师制一般是由在工作上获得公司认可的资深人士,通过分享自身经验及专业知识,对资历浅的员工给予指导与支持。这种建立在深入的、相互信任的师徒关系上的学习过程是持续的,而非一劳永逸的。在我们团队有三个公认的技术大拿,Chaofeng Zou, James Philips和Brian Willett(图6),他们是我们这些职场小白当之无愧的导师。无论是技能上的带领,还是人格上的示范,他们都起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引路人的作用。 图6. Brian Willett (中)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其退休庆祝聚餐中畅谈
Chaofeng一直被我当做梅超风的超风叫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他的中文签名才知道他叫朝逢。朝逢是1982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光化学大家Mark S. Wrighton,并于90年代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因其导师后来在华盛顿大学做校长,朝逢还曾请来了同在华盛顿大学的纳米材料大牛夏幼南教授给研发部开专题讲座,讨论纳米银线技术。清高自负的朝逢的电化学和光化学理论功底极为深厚,总是能从原理上解决关键问题。不仅如此,他做事周全细致,精益求精,我第一次去White City试生产前一天,他牺牲了整个周末跟我email沟通charge card细节,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朝逢不仅在研发上游刃有余,还对经济学兴趣浓厚,尤其擅长股票交易,并收益颇丰,早早实现了个人财富自由。闲暇之余他会跟我讨论《国富论》,并传授我一些投资理念,只可惜我学艺不精,并未一夜暴富。是为一恨! James Philips 在我入职时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是个停留在传说中的人物。他谦和沉稳,擅长配方,他写的实验报告堪称教科书。我与他的结识竟如风清扬之于令狐冲。刚进实验室某日,我正在调配方,准备辊涂(一种涂膜工艺),这时,进来一位60多岁的长者,身形消瘦,面容慈祥,态度谦和。因为刚入职,我不认识他,不敢贸然打招呼。他问了我的名字之后,目光停留在我手中的Mayer rod(一种涂膜棒)上,随即熟练地戴上手套,接过我手中的棒,轻放在一旁,然后问过我样品的有效成分的浓度后,选取了5号棒,行云流水地给我示范了Mayer rod的辊涂。随后,他又教会了我正确使用Doctor Blade Coater(刮刀涂布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正当我懊恼还没顾得上问他的名字时,一位同事过来跟我说,刚才教你做实验的就是James,他的实验技术是全公司最好的。 Brian Willett博士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无论是早期3M时代的配方研发还是后来的涂装工艺,他都劳苦功高。他行事风格杀伐果断,雷厉风行,是真正意义上的Tech Leader(技术组长)。严厉敏锐的Brian还是个细节控。记得有一次,Brian把我叫到会议室,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生怕要接受Brian的单独批斗。因为每次开会,朝逢和Brian的批评最多最尖锐,堪称两大“毒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Brian让我站到讲台上打开不久前我在部门开会时做报告的PPT,他自己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随着PPT的播放,他对我说我PPT的字体太小,坐在后排的人很难看清。然后又跟我一张一张过报告的内容,逐页讨论修改。此情此景,让我有一种当年读博士时江老师为我改论文的感觉,恍若回到了复旦燕园。此时的Brian也一改平日的苛刻,嘴上满是前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盼,眼中却隐隐透着英雄迟暮的哀伤与落寞。其实那时候我们的项目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公司人心涣散,Brian作为元老级别的灵魂人物,应该是已经洞悉到FLEXX黯淡的前景了。 跟Brian的那次讨论不久后,他向公司提出了退休申请,并在和煦温暖的佛罗里达买下了退休房,与早些时候退休的James做了邻居。随着Brian的退休(图7),朝逢终究没能挽狂澜于既倒,洒在将倾的帝国大厦最后一抹余晖也终将消逝,这是诸神的黄昏。从此往后,世间再无FLEXX。 图7. Brian Willett展示同事手工打磨的光荣退休纪念品
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曲终人散后,大家各奔东西。多年以后,我与远在新泽西的好友经常复盘FLEXX项目,我俩共同的感受就是Carestream那几年既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地狱,也是天堂。过往种种,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看来,却是非常的不寻常。 我常常在想,明明就是一派欣欣向荣,明明就是舍我其谁,怎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倒下了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错在误判了ITO的价格会一路走高,从而给纳米银线机会。我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市场对柔性屏的接纳度。其实,直到今天,折叠屏仍没有成为主流。正如Brian在后来给我的email中所言,“and that we all were not successful enough to make Flexx commercially viable. It was quite a tough project though and in some ways ahead of its time!!”(......我们当年未能成功地实现Flexx项目的商业化。这个项目在当时确实极具挑战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前于其时代。) 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齐头并进在工业研究实验室中的重要性。任何优秀产品的问世,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不是少数科学家或工程师所能做到的,而是许多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各级管理人员共同协作、努力的结果。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于我而言,比起学术界的庙堂之高,我更喜欢工业界的江湖之远。因为在工业界,万事均可验证,一切皆有可能。工业界还是学术界,上货架还是上书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诚然,工业界不差钱!不差钱不仅体现在相比起学术界更高的薪资上,也体现在资源调度上的深度和广度。实用性是工业界的另一个鲜明标志。一切不以市场导向为目的的研发都是耍流氓。工业界对实用的追求近乎功利。这样做的后果也很致命,一旦市场发生变化,组织架构说变就变,人员说砍就砍。另外,对实用性的极度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科学研究中最宝贵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恰恰是学术界最让人痴迷和留恋的地方。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热爱并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
小编八卦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远超博士研究生。因此,名校名师的博士研究生名额竞争往往异常激烈。本文作者匡敏博士是小编的博士同门师姐,小编从博士导师江明院士那里得知,匡博士是先生名下数十名博士中为数不多的被先生“一眼看中”的博士候选人。原来江先生当年应邀赴苏州大学讲学,注意到教室内听讲的几十名学生当中,有位与众不同的女同学。只有她自始至终都非常专注,不时微微点头,一双大眼睛充满着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与好奇,且经常与讲台上的先生有眼神交流,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报告后先生与邀请人张可达教授谈及此事,张老师立马说那肯定是匡敏,他最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非常有灵性,是颗好苗子。并当即力荐她到江老师名下攻读博士学位,江老师也是欣然接受。 更有意思的是,江老师课题组做大分子自组装研究,经常需要做大量的电镜测试表征。当时组内的硕士研究生段宏伟是这方面的高手,江老师便推荐他“指导”刚进组的博士研究生匡敏熟悉电镜相关测试操作。由于指导“用心有方”,电镜测试进展顺利,在课题组内被传为美谈。最终两人“自组装”结为伉俪,多年后又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图1)。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