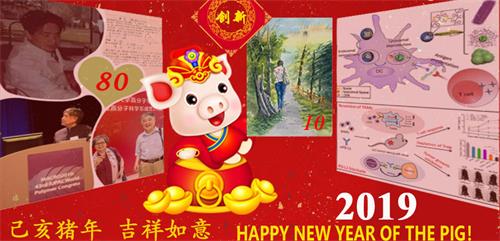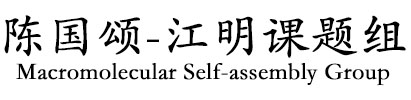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What's New” 先生Adi Eisenberg教授 “What's New” 先生Adi Eisenberg教授 于义松
“离聚物”和“大分子自组装”研究的开拓者,令人尊敬的Adi Eisenberg(艾迪•艾森伯格)教授去世已经两年了。我1995年4月至1999年2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化学系Adi 实验室(图1-3)做了近四年的研究工作,这是我一生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时期之一。近三十年前与先生一起工作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经常浮现于脑海,有些事印象特别深刻。现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也以此表示我对Adi 的敬仰与缅怀。 图1. 我和Adi教授在实验室里
图2. McGill大学化学系楼,离蒙特利尔市中心核心地段200米,坐落在加拿大最著名大街Sherbrooke的中点 图3. 麦吉尔化学系大楼也称为OTTO MAASS BUILDING,Adi教授被冠名为Otto Maass Professor
Adi教授的标签:“What's New” 我在1994年底写信给Adi,希望加入他的团队。他很快就给我回信表示非常欢迎,态度诚恳热情。他从六十年代便开始研究杜邦公司刚开发成功的Nafion隔膜(全氟磺酸隔膜),先后共发表了50多篇相关研究论文,成为国际知名的“离聚体教父”(god father of ionomer)。虽为大家,但他不仅一直给本科生上课,而且每天都会到实验室和大家面对面讨论研究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对新的实验现象充满渴望和兴趣,每天见人就问“what's new?(有新东西吗?)”。一开始我对此很不理解,记得有一次一个已经离开学校25年的师兄回访,看Adi不在,就问我“Adi博士还是每天都问what’s new 吗?” 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他的传统和标签。 他每日问“what's new?”,是他的习惯。但做研究怎么可能每天都有“new”,故对我压力很大。记得在我工作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紧张地做实验时,他过来问我“what's new?”,我没有答理他。但他也不走,就站在我边上,盯着看我做实验。我感觉很不自在,一下竟然火气上来了,问道:我在比利时列日大学当研究员时,Teyssie 教授几乎从来不过问我的工作,我只需定期写研究汇报,通过他的秘书转交给他就可以了。你整天追着问what's new,what's new,是什么意思吗?烦不烦啊?当然了,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可能表达的不那么到位,但他应能听出大意,因为我的愤怒是写在脸上的。出乎意外,他竟然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需要谈谈,好好谈谈(big talk)”。我也意识到自己失礼了,于是就停下实验,随他到办公室谈了很久。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向他发火的中国人。他很抱歉,并答应以后不再追问我的工作进展。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他以后有什么需求可以提出,我会记下来,并贴在办公室桌上,根据重要程度来安排具体时间。在那以后,我们都遵守约定,“what's new” 的确少了许多。但有时是因为我的英语表达能力问题,有时是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仍然不时需要进行“big talk”,甚至会长达数小时。一般来说,这种因摩擦而导致的谈话,结果通常并不都是愉快的。但奇怪的是,于我们俩之间而言,这不但没有增加彼此间的隔阂,反而日渐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和师生情谊。多年后回想起来,Adi对待学生如我的方式和态度,显示了其大家风范。我对McGill生活的回忆是美好的,甚至觉得有点甜蜜。
Adi教授对待科学的态度:严谨与开放 说到严谨,首先想到的是Adi会亲自修改团队发表的每一篇论文。他改文章的方式是独特的。改文章时,他都要求我们作者和他坐在一起,面对面逐字逐句地修改,反复推敲。这一过程不仅极大提高了我们的科研论文写作能力,也强化了我们的英语水平。特别地,他对论文的前言部分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列出前人的工作基础,注明出处,所以Adi组的研究论文总是有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这既是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自信,也是对前人工作基础的尊重,更是科研工作者应有的严谨与科学。与那些为了强调自己的“创新”,刻意对前人的相关基础避而不谈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说到教授对于科学研究的开放态度,有几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我加入团队的时候,课题组的张黎峰已经发现大分子自组装现象,并在Science上发表了论文。他的第二篇文章也正在撰写当中,在组会上讨论时,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分子结构固然重要,但溶剂可能影响更大。大家都不同意我的观点,表示试过我的想法,并没有发现有影响。这时候我作为中国人不服输的倔脾气就上来了。小组会结束后,我立马就回到实验室开始做实验,很快就验证我的想法。再与Adi讨论时,他很是兴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让我抓紧时间补充数据、写论文。然后就是每天和我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改,很快我们就将论文发给Science编辑部。遗憾的是,编辑部回信说我们组已经连续发了两篇了,再发不太适合。最后这篇论文很快便发表在JACS上(图4)。这篇论文是Adi团队几百篇大分子自组装文章中的第四篇。再有一个例子是,我不赞成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观点:聚合物链段的高玻璃化转变温度是形成大分子自组装现象的关键。于是自己合成样品,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我的观点。这同样得到了Adi的支持,论文发表在Langmuir上。还有,我不赞成大分子自组装是一个热力学平衡过程。张黎峰后来设计了一组长时间实验,验证了我的观点,最终结果发表在顶级刊物Physical Review上,我并没有参加相关的实验工作,但就因为这“一句话”,就被Adi列为作者之一。从以上这几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出Adi教授对科学研究的开放心态,他鼓励大家去质疑已有的结论,甚至推翻它,让科学研究向前推进。他经常告诫我们:“If you get what you want,it is good;if you get what you do not want,it is even better!”(如果你得到了你想要的,这很好;如果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这更好!)。这简短一句话,让我学会了如何在研究中,从看似所谓的失败中捕捉成功的影子,让我受益终生。
生活中的Adi教授:温情且可亲 Adi是一个和蔼可亲,愿意和别人分享生活经历的充满温情的人。我到了蒙特利尔后,他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家庭和孩子,经常问起。他曾经和我们说,他们家族是波兰犹太人,在二战中整个家族上百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他们从波兰到了德国再到美国。他虽然在加拿大工作了一辈子,却是一位美国公民。他并不完全遵守犹太人礼节,经常请组里人到唐人街中餐馆吃饭。他会和西方学生开玩笑,让他们吃“凤爪”。有一次我在比利时的老板Jerome教授来蒙特利尔开会,顺便来实验室看Adi和我。晚上Adi要请Jerome去吃蒙特利尔最出名的“smoked meat”(熏肉),被比利时美食家Jerome一口拒绝:“I never eat America food” (我从来不吃美国餐)。最后只能去了一家高档法式餐厅,而且还点了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这让一向节俭的Adi非常心疼。为了弥补他的“损失”,我提议请他们两位到我家吃顿饭。我太太为他们做了一桌丰盛正宗的中国菜,他们吃的赞不绝口。当晚的话题也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展开。离开麦吉尔大学后,他来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参加我一个好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在一家中餐馆请他吃饭。他说他刚去了中国,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叹上海的繁华、安全和美食,更惊讶一家餐馆居然能占据7层楼! 我在加入Adi团队以前已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且拥有丰富的高分子的合成与表征经验。所以在Adi实验室我也算是资深研究人员,经常会帮助课题组或Adi朋友的博士生合成各种新的高分子,与他们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也结识了不少好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教授,甚至名校的副校长。印象比较深的是化学系实验室的一位犹太女管理员,是Adi很多年的好朋友。Adi让我花点时间用一种当时比较新的表征方法,分析嵌段高分子的结构,相关研究结果我写了两篇论文。Adi和我商量是否可以让那位犹太女管理员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因为她需要文章来保住在麦吉尔大学的工作,否则将面临失业的危险。我虽然觉得有些不开心,但最终还是同意了。Adi瞬间变得很开心,并许诺将来一定会帮我写最好的推荐信。看到他为保住自己好朋友的饭碗而委身求我的“可怜样”,和事成后开心喜悦的表情,我之前的不悦也立马消失并为之感动。 回忆和Adi在一起工作的几年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他是我一生中接触到的最亲近的外国朋友,亦师亦友。能够和这么伟大的高分子科学家工作是我最大的荣幸。我永远怀念他那慈祥的笑容!愿先生在天堂安息!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