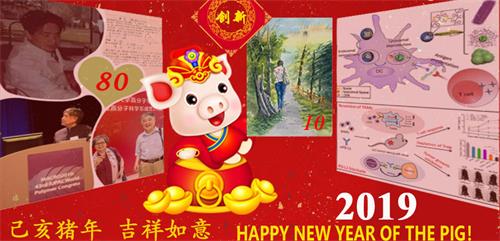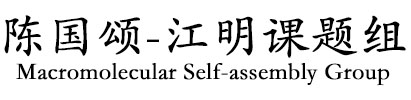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3,匹兹堡扬弃 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3,匹兹堡扬弃
王锦山
2024.02.17. 美国罗切斯特 2024.03.9. 中国上海
1月15日本系列之续2发表后,一直惦记着早点完成续3。但手头缺点资料,依稀记得可能在美国家里几次搬家未打开的箱子里。正好,春节到了,给自己“放假”几天去趟美国。大年三十半夜到家,稍息片刻,花了足足4个多钟头,终于从地下室存放多年的三个纸箱里,幸运地找到了尘封近30年想要的大部分资料。 接下来的几天,索性不倒时差了。夜深人静,默默地翻阅着几份找到的资料,静静地敲打着心中的纷飞思绪,勾忆起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Matyjaszewski教授(老马)实验室度过的短暂但却富足的11个月[1,2],特别是最初4个月中扬弃ATRP的心路历程。 从93年10月10日我正式回复老马接受他的offer算起,历时近10个月,于94年8月8日,拿到了赴美工作签证(H1-B)。说实话,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有机会直线或曲线去美国深造或工作,着实不易。我当时真是激动和憧憬,由衷感谢老马给予的机会和办理签证时的倾力相助。 与大家细说在老马实验室扬弃ATRP之前,先穿插陈述一段相关的故事,以便大家对我来美后开展ATRP研究的大背景有大致的了解。 我飞美的前几个月,老马和来自罗马尼亚的博士后,Dr. M,在美国化学会Macromolecules期刊94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of Vinyl Acetate”的文章(下称VAc活性聚合)[3](图1)。 图1. 老马和Dr. M(本文第一作者)在Macromolecules发表的一篇醋酸乙烯酯活性自由基聚合的文章
这篇文章题目非常简短,只有三个词:醋酸乙烯酯(vinyl acetate, VAc),活性(living),自由基聚合(radical polymerization)。但每个词都力重千钧。这是历史上第一例醋酸乙烯酯活性聚合!学过高分子化学的人都知道,烯烃类单体中,VAc只能进行自由基聚合,其他烯烃类单体如苯乙烯、丙烯酸酯等不但可以发生自由基聚合,还可进行离子型或其他聚合。之前的大量研究表明,VAc极难进行活性聚合。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接近于摘得了活性自由基聚合的皇冠。其潜在的意义在于,既然这个体系可以使VAc活性聚合,那其活性种就应该是自由基,所用催化体系极有可能是普适的,可广泛应用于其他单体的活性自由基聚合。 另外,Ziegler-Natta发现定向聚合以来,人们对含有有机金属的多元催化体系特别感兴趣。老马报道的VAc活性聚合体系正是这样的三元络合物体系,即路易斯酸(Lewis acids,如三烷基铝,AlR3),路易斯碱(Lewis bases,如联二吡啶,2,2'-Bipyridyl, bpy)和稳定的自由基(Stable radicals,如2,2,6,6-tetramethyl-l-piperidinyloxy, TEMPO)。这三者的组合非常独特,给当时孜孜探究活性自由基聚合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震惊高分子合成界。全球众多知名实验室都相继重复、并希冀发展老马这个新的活性自由基聚合体系。我真为老马高兴,也为自己选择了老马而自豪[4],对不日即将加盟老马团队进行活性自由基聚合研究的未来更加神往和充满期待。 可是,一到老马实验室,我立马感到很是蹊跷。那时实验室只有2人在继续从事VAc活性聚合的进一步研究。一位是来自日本某公司的访问学者(自带经费),另一位是来自波兰的在读美女博士生(97.06毕业,后面还要讲到她)。其余3.5位(一位在职博士生只是周末才来实验室,故算0.5人)博士生中,只有一位在做与活性自由基聚合有关,但并不是VAc聚合的研究。我进实验室4个多月后才见到了Dr. M。据说她已找到一份某公司的工作。另外,实验室的气氛也有点闷,丝毫看不出从事VAc活性聚合研究的二位同事有“摘取皇冠”的激情和活力。 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验室一直没人能重复VAc活性聚合实验。原来这样! 现在还记得,95年春我应邀去美国杜邦公司位于宾州费城的Marshall Laboratory[5]做ATRP学术讲座时,证实了该说法。当时接待我的是杜邦终身研究员Fryd博士[6]。讲座结束后,他和几位骨干在一家西餐厅招待了我。席间,Fryd对我直言:您的工作听上去很好,但不知是不是如Matyjaszewski(老马)教授前期报道的VAc活性聚合那样?我们无法重复他们的实验,那篇文章中的数据有点像是伪造的。听到Fryd不客气的问话,我错愕,也极其尴尬,无以回答。 回来后,我把Fryd说的话告诉了老马。老马略显沮丧地对我说(大意是):Yes. After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experiment records, I found that the data were somehow manipulated. You know, I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build good reputation in US. However,it was just ruined overnight(是的,仔细检查了实验记录后,我发那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为造假。你知道的,我在美国非常努力工作来建立好的声誉。但,一夜之间被毁了!)。 94年对老马来说有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上半年,高分子合成化学界为他新报道的研究工作鼓掌叫好,下半年开始,许多知名实验室陆续传来消息,完全不能重复他们的VAc活性聚合实验。尤其是来自杜邦这种巨无霸公司的负面评论,人们不禁对老马团队的学术诚信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我是在事先不知晓这种尴尬局面的情景下,兴高采烈地来到老马实验室的。刚听说这事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还真有点失望,也感到受到了冒犯。但,我想,我来老马实验室是有自己的原则、理想和追求的。因此,后来无论是对老马的信心,还是自己干事的劲头,都没受这事影响。 说到自己,我当时很清楚一点。经过在Teyssie教授实验室5年的不凡历练,与89年从上海去列日读博时相比,自己的心态、学术直感和能力,都已不可同日而语。怀揣顶尖大学A+博士学位证书和16篇已发表和待发表的一作学术论文,还有已形成的ATRP雏形,我全无5年前那种心里落差和忐忑不安的窘态。相反,我信心爆棚、踌躇满志。 之前,我与老马其实已在不同场合见过三次[7]。我打心眼里喜欢、欣赏和敬佩老马。他不仅治学严谨,学术思维敏捷,对活性聚合有深邃的认知,又是一位自第三世界国家波兰到美国追梦,靠自己打拼,在世界顶尖大学CMU获得终身教授(tenure professor)职位的励志榜样。此外,他当年40岁开外,活力四射,又长得特帅,且总是满脸笑容,亲和力特强(图2)。 9月初到匹兹堡后,老马安排我和家人先在一家旅馆住下。几天后,为了方便上下班,我在离实验室不到10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系里一位来自山东、即将去高通公司工作的博士毕业生Joe,送了我几件她们家用过的桌椅。此外,老马主动告诉我,他有一个大大的床垫可以借给我。 图2. 第一次见到老马是92年7月在德国美因茨召开的“阴离子聚合及相关聚合反应”研讨会上(参会人员合影)。Sawamoto(黄箭头)、老马(红箭头)、我(蓝箭头)、备受质疑的VAc活性聚合文章的第一作者,Dr. M(绿箭头)。插图(左上角)中的二位是当年参加会议的老马(左)和京都大学的Sawamoto教授(右)
记得是到匹兹堡后的第二个周六下午,我正在打扫新租住所,接到老马电话,说给我送来了床垫。我赶紧下楼迎接,看到楼前路边大约200米远处停着老马的车。至今记忆犹新,只见老马肩扛几十斤重的厚厚的床垫,朝我走来,并带着微笑向我招手。此情此景,我不禁肃然起敬,感激之情油然升起。老马可是世界知名教授啊!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一位导师教授如此接地气和暖心。我当时就想,作为来自波兰的第一代移民,他与我们一定有相似的经历,理解我们漂洋过海,寻找更好机会和前途的苦、难和思。后来我没有再买床,一直睡在老马借给的床垫上,直到离开匹兹堡。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忆起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我对老马的感恩之心依旧浓浓。 在老马办公室正式报道上班见到他时,我们已是格外熟络和亲切。我感叹终于结束了长达10个月的等待。 寒暄一番后,老马首先给我阐述了他基于当时快速发展的阳离子等活性聚合思考而得出的普适活性聚合理念,并让我读一读他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8](我个人以为,这篇文章是我当时读到的最经典的新活性聚合理论文献之一,具有超高的战略视角和深邃的理性思索)。第一次听完他的系统的活性聚合理念和仔细研读了他的文章后,我真感到醍醐灌顶,让我对减活-促活活性聚合机理的理解从过去较为感性的认知一下子上升到了理性高度,对我以后的研究(包括发现ATRP)有着关键的指导意义和影响。 一切就绪,终于可以开始大干一番了。 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好事一定得多磨。当我急切地向老马展示我的ATRP雏形和研究计划时,老马告诉我,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Scott Gaynor(97.04获博士学位),已经在从事他称之为degenerative transfer polymerization (退化转移或衰减链转移聚合,以下简称“退化转移聚合”)的研究,并让我参与进来。 啊! Scott正在进行的有机碘化物引发、自由基催化的退化转移聚合就是我在列日几经周折形成的ATRP雏形啊[9]。听到这个消息,可想而知,非常惊讶之余,我有点不知所措,也特郁闷,更有一种急迫感。 到这时候,我能做什么? 也好!尽管做起活性阴离子聚合实验,我很得心应手。但,在活性自由基聚合领域,我毕竟还是一个只有猜想和雏形的小白,从未碰过相关实验。以此入手,一来,可以练练手,二来,可通过不断实验,加深对ATRP的认识和理解,由此也许可以进一步发现新的活性聚合体系。我一向都是积极思考者。 还是尽快进实验室做实验吧,我自己催促自己。 不过,刚进老马实验室开始做实验时,我着实还是有点别样的吃惊和另外一种反差。比起Teyssie教授实验室大而全、应有尽有,老马实验室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简陋,条件也很一般。吃惊归吃惊,反差归反差,但我更敬佩老马了。何等的不易和了不起!这样的条件,照样做出了世界顶级科研成果。 9月11日(周日),我正式开始做实验。短期目标是用退化转移聚合方法合成聚苯乙烯/聚丙烯酸丁酯嵌段共聚物。对我来说,用Scott已经开发的引发体系合成共聚物,小菜一碟。接下来的2个月里,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每天14个小时左右泡在实验室,成功制备了20多个不同的样品。 就在这个时候,老马和Scott已写好了一篇通讯文章,准备寄去JACS发表。我看到最后一稿作者排名的顺序(老马第一,Scott第二,我第三)时,好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Scott不是一作?老马的回答很简单:This was my original idea(这是我的原始想法)。我想起老马曾对我说过:If we could make this a perfect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we would get everything we want(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发展成真正的活性自由基聚合,我们将得到所有我们想要的)。此时,我隐隐约约感到,老马对这个退化转移聚合研究非常看重和寄予厚望!看来,VAc活性聚合文章引起的负面影响和难以预料的持续效应,是个硬伤。需要尽快发现一个真正的活性聚合体系,给老马和实验室正名。 非常遗憾,这篇通讯稿件寄出大约一个月左右,JACS编委寄回了审稿人的书面意见。无一同意该文发表在JACS上。有一位审稿人的大意是:概念叙述过多,实验数据不够令人信服。 他们随即稍作修改,把它寄到了Macromolecules,最终在95年第6期上发表[10a]。感谢老马,感谢Scott。这是我历史上第一篇活性自由基聚合文章,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老马一起发表文章。 但是,这时我已经明显感到碘原子参与的退化转移聚合(也是我的ATRP雏形)并不是理想的活性聚合体系:聚合物分子量小于10000时方可实现某种程度的可制;均聚物的分子量分布(PDI)较宽(PDI > 1.4);嵌段聚合物分子量分布更宽(PDI:1.6 – 2.0),且有大量的均聚物残留。 我直感这类体系没有太大希望。我对自己说,是放弃继续花时间进行这类实验的时候了。其实当时确实还有点不舍,心里也有点酸和疼。但,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不小的挫折,反而刺激了我的那种永不服输、乐于与天斗的劲儿。我有个逻辑,科学研究的挑战就如长跑遇到的生理极限一样,只要永不放弃,坚持,挺过去,继续,就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而一次竞跑,遇到的挑战越多,成为赢家的概率就越大。我喜欢逆向思维,更喜欢挑战带来的快感。 在列日读博、工作的后2-3年间,我不止一次有过难以言表的思维突变、灵感大发的亲身体验。那时候,每当出现新的挑战,自己的精力就会像激光一样高度集中,迸发灵感。更有甚者,连续不断的高度精力集中,有时会让我冥冥之中感知到,“梦幻”的眼前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向前寻得解决问题的钥匙。在老马实验室扬弃ATRP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类似的心路历程。 94年11月上旬开始,为完成第二篇论文所需的补充数据[10b],继续进行退化转移聚合研究的同时,我自己也已开启了迎接挑战,构思真正的ATRP的模式。 几个星期里,我辗转不寐,茶饭不香,魂不守舍,心系真正可以活性聚合的ATRP,思絮缭绕,苦思冥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复盘”在Teyssie实验室孕育ATRP雏形的全过程。 12月初的一天,当从Quirk教授的“裸”阴离子GTP活性聚合,到Curran教授等的可控小分子原子/基团转移自由基环化/加成反应,再到我的基团/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反应(ATRP)雏形,逐个梳理的过程中,我猛然想起GTP其实有二种不同的催化体系:一是Quirk教授揭示的“裸”阴离子催化GTP活性聚合,另一个是反应机理研究得尚不透彻的Lewis acid,如ZnCl2等催化活性GTP[11]。 这时,我突发奇想,既然有Lewis acid(ZnCl2)催化的GTP,小分子自由基化学领域是否也有金属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加成反应?带着这个全新无厘头疑问,我一头扎进了CMU Mellon Institute图书馆(图3)。 图3. Mellon Institute(MI,右)和MI图书馆(左)
天啦!与当年在列日大学理学院图书馆偶阅Curran的基团转移自由基加成文章带来的惊喜一样,在诸多顶级期刊,如JACS和JOC(有机化学志)等中,我一下子查到了十几篇金属催化的卤原子转移自由基环化和加成反应的文章! 仔细读过其中一篇文献[12],我发现其反应机理就是我所期望的原子转移自由基(环化)反应(图4)。与Curran报道的自由基催化的硒基团/碘原子转移自由基环化或加成反应相比,主要有二点不同:一是使用相对比较稳定的R-X(X=氯原子)代替R-X(X=碘原子、硒基团);二是使用催化能力更强的转移金属络合物,如CuCl/bpy,代替自由基催化剂。 图4. 典型的转移金属催化的氯原子转移自由基环化反应机理
在接下来的2周时间里,我一口气研读了几十篇小分子转移金属催化的卤原子转移自由基环化/加成反应文献,对各类体系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自己的活性聚合研究经验,改进和发展了小分子ATRA的实验条件和体系,如催化体系、单体选择、溶剂选择和反应器设计等,设想出初期的金属催化ATRP实验思路,并根据实验结果不时调整反应条件。 对实验科学而言,一个好的想法只是成功的一半,只有附着于严格、高质量的实验手段和技巧,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使用自己在Teyssie实验室练就的吹制玻璃“金手”技术,我设计和制备了用于ATRP研究的微型玻璃反应器(容积约5 mL)(图5)。这个微型反应器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它是我能够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得到最原始、可靠的金属催化ATRP实验数据的保证。 • 在密封微反应器中聚合,保证反应不受外界不必要因素的干扰; • 极易在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上进行本体聚合,转化率高; • 在同样反应条件下,可以同时进行若干聚合反应实验,即小“高通量”实验,大大加快筛选试验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 ATRP反应经常需要通宵进行,在密封微反应器中安全可靠。 1.用酸、碱、纯水清洗过的玻璃管; 2.吹制制备微反应器,并放入微小磁力搅拌子(红色); 3.对玻璃管进行局部“瘦身”后,定量加入反应原料,然后循环进行冻融脱气、充氮三次; 4.真空状态下封管。将密封的微反应器浸入带有磁力搅拌的恒温油浴中,进行聚合反应。反应停止后,打碎玻璃封口,进行各种后处理。
图5. 我利用氧气枪吹制的用于ATRP研究的微反应器(容积约5 mL)
后来发现,ATRP实验并不一定需要如图5所示的复杂而苛刻的反应器和条件。但,刚开发一种新化学反应时,非常有必要剔除一切可能存在的非正常影响因素,以期尽快成功。成功后,可以放心去优化各种反应条件,进行深入,甚至是降维打击式的研究。 其实,在尝试金属催化ATRP实验前,我曾向老马报告过我的想法。老马当时对此不是太感冒。他说,Dr. M和另一位博士生已经尝试过很多金属化合物参与的自由基聚合,留下了几本厚厚的实验记录本,但却没有成功的案例。 虽然老马还是要我专注于退化转移聚合的深入研究,但感激的是,他不但不反对,还给了我足够的空间,使得我可以自由发挥,探索新催化体系。 从94年12月13日开始,我动手做第一批CuCl/bpy催化的ATRP实验(同时进行5个实验),至12月23日,10天时间里,总共进行了44个微反应器中的ATRP聚合实验。我如激光一样聚焦在“微反应器里的ATRP”,每天14-16个小时在做实验,及时调整反应条件,回家后继续整理实验数据。 圣诞前夜,Mellon Institute大楼外灯火辉煌。可老马实验室这一层,只有我的实验室和老马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实验室的其他人都已放假离开了学校,去不同地方,与家人或朋友欢乐团聚,共度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假日–圣诞和元旦。 大约7时许,我无比激动地拿着刚刚得到的、带着打印机油墨香的二张实验数据图(图6),飞奔来到老马办公室。在我将图递给正在大口吃着水果橙子的老马时,想到明天就是圣诞了,脱口而出:This is the gift from the god to you(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美式幽默了一把。 老马紧盯着二张图,仔细端详。刹那间,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连说: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我晓得,老马一眼就能看出了这二张图的意义和份量:一个梦寐以求、实实在在、真正的活性聚合体系诞生了!我也能想象,那时老马比谁都更感慨这二张图对他的实验室意味着什么! 图6. 1994年12月圣诞前夜得到的证明转移金属催化苯乙烯ATRP活性聚合最原始的二张实验数据图,实验条件见文献[13]。图中红字和标记是当年老马添加/修改的。
图6中的Figure 1(左图)是转化率(Conv.,曲线)和ln([M]o/[M])(直线)与时间(t, min)的关系图。苯乙烯ATRP反应至90%以上转化率时,ln([M]o/[M])随时间变化还保持着直线关系,说明反应体系中活性自由基的浓度基本不变,终止反应不显著。 图6中Figure 2(右图)是数均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与转化率的关系图。图中的小黑方块是不同转化率下,实测的聚合物数均分子量,Mn,SEC。虚线(老马建议改成实线,solid)是不同转化率下的理论数均分子量,Mn,th。黑点与虚线基本吻合,说明分子量随单体转化率增加而线性增加,且可设计,也说明引发剂R-X和形成的大分子卤化物 P-X浓度接近,其“引发”单体的效率高。图中田字方块是不同转化率下,实测的分子量分布值,MWD(老马改成了Mw/Mn)。在整个转化率范围内,分子量分布指数相对比较小(1.3–1.45),说明聚合反应生成了尺寸较为均一的大分子链。 上述Figure 1 和Figure 2二张图一起可以初步确认我得到了一个活性聚合体系。 此时此刻,我也是不能自已!Teyssie实验室形成的ATRP雏形终于在老马实验室成功被扬弃了!一个新高分子化学反应,转移金属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真正的活性自由基聚合,终于诞生了! 从老马办公室回到实验室后,我依然心潮澎湃。第一时间给我最亲近的同学和一辈子的好朋友,在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读博士的程海涛打去长途电话,情不自禁地与他分享了这个发现。电话那头也是激动不已。 接下来,我一鼓作气,一边在实验室连续作战,一边开始构思撰写第一篇金属催化ATRP通讯论文。 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实验室,没有圣诞,没有元旦,没有干扰,只有ATRP,期间,全部使用市售的1-phenylchloride (1-PECl)做引发剂,CuCl/bpy为催化剂,130 ℃条件下,在封闭微反应器中,实现了苯乙烯及其他单体的ATRP活性聚合;通过核磁共振分析确定所得聚合物末端基团的结构,证明了Cl原子基团转移的存在;从添加阻聚剂可以阻止苯乙烯单体聚合反应发生,和所得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立构规整性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反应就是自由基聚合。不间断地干到95年1月11日,得到了第一篇ATRP通讯论文所需的关键数据。 没几天,我把写的通讯论文初稿整整齐齐呈送给了老马(图7)。 老马对稿件的主要内容没有太大异议,但我们在二个点上争持不下。第一点,他不同意用ATRP这个术语。如图7所示,他用红笔把原始稿件题目中我写的“Atom Ttransfer” 两个单词圈起来,并用“Controlled”来替换,不管当时如何解释,都难改他的初衷。这让我记起,在之前的一次小组会上讨论退化转移聚合时,老马也断然拒绝过我提议的含碘的ATRP这个术语。他希望这篇通讯文章用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可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我的想法。第二点,我特坚持投稿JACS,但他更希望一炮即中和快发,建议投稿Macromolecules。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俩对这两点僵持不下。 图7. 我写的第一篇最终发表在JACS上(图8)的转移金属催化ATRP文章的初稿(1995年1月完成)。文稿中红色字体是老马修改的部分。老马当时并不赞成我提出的“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ATRP),而是坚持用“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
与此同时,老马非常审慎地把我的稿件发给了陆续返校的几位博士生和Dr. M,征求他们的意见。 所有人都相当惊愕,圣诞节前,我和Scott还在折腾退化转移聚合,怎么十几天假期回来,眼睛一眨,就有了这么大的发现,而且一篇通讯文章已经写好了?可以想象,读了我的稿件,各人反应不一。 一位从事含硅聚合物研究的博士生捧着厚厚的物理化学常数手册来到我的面前,指着CuI/CuII氧化还原常数说:这不支持你的氧化还原反应促成的ATRP机理。我说:是的,CuI/CuII氧化还原常数不支持,但与bpy的络合可以改变一切。他想了想说:也许。 不几天,他看到我在94年第18期Macromolecules上连发四篇第一作者论文后[14],走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你原来是Teyssie教授的博士生,不是他的博士后啊! 最尖锐的评论来自那位波兰美女博士生。她在小组会上告诉大家,不能重复我论文中的实验,我的方法不行。我知道,她是被那篇VAc活性聚合的文章耽误时间最多的人。2年多时间内,做了若干实验,还没有取得像样的博士学位论文实验数据。我猜,她可能还以为我是又一个VAc活性聚合的“发明”者。 理解美女博士生的苦衷,我也知道她的问题所在。我是做实验条件极其严苛的活性阴离子聚合出身的。所以刚进老马实验室时,我就发现,相比而言团队中许多人的实验操作不够严谨和规范。譬如,他们习惯性地用橡皮塞封口的瓶子作聚合反应容器。但高温反应时,橡皮塞会吸收大量的溶剂和单体而溶胀,致使体系中单体浓度的测量数据不准。他们还用注射器针头多次刺破橡皮塞取样,计算单体转化率。这样的操作,肯定难以得到准确、可靠的动力学实验数据。 会后,我把她叫到我实验室,向她示范了我的实验操作后说:我给你制备几个微反应器,你按照我示范的方法重复一次。第二天,她笑盈盈地跑来对我说:Thank you, Dr. Wang. It works(王博士,谢谢你。你的方法可以的)。“Of course”,我自语。 最有意思的应该是Scott了。Soctt是那时我在老马实验室里见过的领导力、执行力、责任感最强,职业素养也很棒的在读博士生。他虽年轻,但很成熟。我很喜欢他本人和与他共事。 他一个人在他的实验室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闷声不响地重复了我稿件中的大部分实验。小组会上,他正式作了个专题报告,最后一本正经地给出了结论:It is confirmed that Dr. Wang's system works well(经证实,王博士的体系运行效果良好)。 最不从容的当是Dr. M了。她只给我留下了一句话:如果这是真的,你就get everything了。看来,在实验室,老马不止对我一人说过类似get everything之类的话。 但几个星期过去了,老马却还没再找我讨论发文章的事,我急。不得不说老马这次真的很认真和谨慎! 一天,听说老马要去德国BASF参加项目汇报会,我趁机复印了几篇有代表性的自由基催化和转移金属催化的有机小分子ATRA的文章,送给老马,请他在路上有时间时读一下。 大约一周后的小组会上,刚从德国回实验室的老马满面春风,谈笑风生,大家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和兴奋。他宣布了几个好消息,BASF非常认可我们的工作,不但同意延续合作,还增加了资助经费,并希望买下我们的ATRP专利。还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多出成果,为实验室多拿资助。 出乎意料,老马给我加薪20%,并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更重要的是,他完全同意我当初的提议:使用“ATRP”这个术语,稿件寄JACS发表。我猜测大概率是BASF的认可和那些小分子ATRA的文献一起说服了他吧。 我们重写了稿件的引言部分,使得ATRP概念源于ATRA的表述更加直接和清晰,还加了一些内容,对文字又做了进一步的润色,标题也加上了Controlled/"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于95年2月中旬邮寄JACS编委。毫无悬念,所有审稿人的意见都非常正面。我们只做了小修,就很快正式发表[13](图8,编辑部95年2月16日收到稿件,5月1日正式发表)。
图8. 我和老马发表的第一篇转移金属催化ATRP文章。引以为豪的是,ATRP是高分子科学发展史上首次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发明人(论文第一作者)的新高分子化学反应
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高分子界的轰动,仅过了一个月,美国化学会C&EN 周刊 在1995年6月5日的第46-48页上, 对这篇论文进行了专题报道。但该报道存在很大的失误:没有写上第一作者的名字。为此,老马立即专门致信C&EN 编委,在6月19日的那一期(图9)上对此做了及时更正:“......Please note that ATRP was co-developed with Jin-Shan Wang, who is a coauthor of the cited paper and whose name should not have been omitted in your story...... ”(请注意ATRP是与王锦山(Jin-Shan Wang)共同开发的,他是那篇论文的合著者,你们已报道的故事中不应该遗漏他的名字)。 图9.老马在1995年6月19日的美国化学会C&EN 周刊上撰文指出我(Jin-Shan Wang)是ATRP的共同发明人,之前的报道中不应该遗漏我的名字
95年2月开始,老马增派了二名CMU化学系非常优秀的四年级本科生给我做助手,我如虎添翼。至95年7月底我正式离开匹兹堡前,又成功开发了一种新的ATRP反应,即传统自由基引发剂(如AIBN)与高价转移金属络合物(如CuCl2/bpy)结合催化的反-ATRP(reverse ATRP),并撰写了后来相继在Macromolecules上发表的一篇ATRP 研究全文[15a]和一篇通讯文章[15b]。 在撰写这篇研究全文的过程中,我的活性聚合理念也得以进一步升华。结合研读老马的那篇“Ranking Living Systems”经典文章[8],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到,在类似ATRP的新活性聚合体系中,反应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链终止反应。但在一定的转化率范围内,只要增长速度远大于终止速度,且通过休眠种-活性种(ATRP中的P-X和P自由基,P:大分子链;X:卤原子)快速转换,保证存在低而恒定的增长自由基活性种浓度,活性自由基聚合就可以实现。 在上述研究全文中,我们历史上第一次用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ATRP中原子转移和自由基的活性聚合属性和关键作用,及其他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我和老马的活性自由基聚合学术思想。30年来,文章中的主要论点得到了无数研究者的检验和论证,成为ATRP最经典的文献之一,也是Macromolecules创刊40年来他引最多的十篇论文之一[16]。 2020年2月,美国NIST(国家标准局)的Dr. Beers(老马的博士,2000.08毕业)应Macromolecules编委之邀,在纪念高分子鼻祖Staudinger发现大分子100周年之际,就这篇研究全文写了一篇客观、精准、精辟的专评[17],值得一读。 ATRP是高分子科学发展史上首次以中国科学家为主要发明人的新高分子化学反应。30年来,ATRP的发现给活性自由基聚合学术研究和产业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2017年,Macromolecules将可控自由基聚合(ATRP,NMP以及后继开发的RAFT等为代表)排在1967-2017年50年间高分子科学领域取得的10大成就的第1位[18]。源于ATRP,科学家们现将这类新的活性自由基聚合也称为RDRP(reversible deactivation radical polymerization)[19]。2019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成立100周年之际,向全球化学家征集意见并最终评选出了10项最有可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化学创新,RDRP位列第九[20]。 ATRP的发现也完全改变了老马实验室的研究方向。86年至96年11年间,老马的7位博士毕业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课题无一与活性自由基聚合有关(活性阳离子1人,含磷聚合物2人,含硅聚合物4人)。然而,95年入校后的博士生研究课题都围绕ATRP及相应的活性自由基聚合而展开。有趣的是,那位美女博士生和Scott都将原来从事的VAc活性聚合和退化转移聚合研究课题改成了ATRP相关的。
结语 在“写在ATRP问世30周年之际-3” 即将完稿之时,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发明ATRP的整个历程(图10)。 在列日,源于Quirk教授“裸”阴离子催化基团转移聚合(GTP)机理与我前已形成的活性聚合理念产生的激烈碰撞,我产生了类似于GTP的活性自由基聚合(减活-促活平衡)猜想(1);尔后,从小分子原子/基团转移自由基加成反应/环化反应(ATRA)(催化剂是自由基)中得到灵感,“移植”ATRA概念形成了自由基催化、碘原子转移的ATRP雏形(2);在老马实验室,ATRP雏形得以进一步扬弃,我改进和发展了小分子合成中转移金属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加成反应(3);最终发明了真正的ATRP活性聚合(4)。 我想强调,ATRP从灵感火花闪烁,到概念提出,再到质的扬弃,最后得以成真,自始至终,我主要就是一个dots connector(点点连接者)。Teyssie和Matyjaszewski教授(尤其是Matyjaszewski教授)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键影响至关重要。 图10. 历时3年经历了4个阶段,我发明了金属催化的ATRP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JACS发表我们第一篇ATRP通讯文章[13]的3个月前,Macromolecules发表了日本京都大学Sawamoto教授等的金属催化甲基丙烯酸甲酯活性自由基聚合的通讯文章(95年2月1日)(附件一)[21]。尽管Sawamoto教授发现的这个反应与我们提出的ATRP的机理基本一致,大家也习惯将其归于ATRP一类的活性自由基聚合范畴[22],几十年来,Sawamoto教授从来没有使用过ATRP这个术语。 与图10展示的发明历程完全不同,Sawamoto等人的灵感直接来自于他们致力研究的活性阳离子聚合[21, 23]。尽管我们的灵感来源完全不同,但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可谓异曲同工。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科学研究现象。 可以说,任何科学发明的曲折历程一定与发明者本身的学术背景和科研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专长于活性阴离子聚合,我的ATRP猜想源于GTP阴离子聚合(图10)。而Sawamoto等精于活性阳离子聚合,自然而然,活性阳离子聚合激发了他们的活性自由基聚合灵感(附件一,图11、12)。 也就是说,科学发明可源于不同起点,产生出不同设想和概念,经过不同大脑的点点相连和酝酿,最终可以到达同样的终点。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殊途同归”和西方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所表达的类似哲理所在吧。
鸣谢 江明院士和郭明雨教授本着科学、严谨、认真的专业态度,精心耕耘,以国际顶级期刊水准的要求创办“旦苑晨钟”,使之成为传播科学文化思想且兼顾趣味性、科普性的自媒体公众号。在本文自酝酿至发布的全过程中,我深深感触到他们为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承,建筑不一样科坛家园的炽热情怀和奉献精神。谢谢他们!
参考文献及备注(Reference and Note)
1. 1965年,卡内基理工学院与梅隆工业研究学院合并,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英语: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缩写为CMU)。老马所在的化学系在梅隆理学院。迄今为止,CMU共有包括74年化学奖获得者、曾任梅隆理学院院长的高分子巨匠Paul Flory在内的20人获得诺贝尔奖,13人获图灵奖,7人获奥斯卡金像奖。 2. Krzysztof Matyjaszewski,我的博士后导师,大家都称他Kris,中国人昵称老马,生于1950年4月8日,波兰裔美国人。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波兰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罗兹理工大学)学习化学。72年毕业于Petrochemical University in Moscow(古布金俄罗斯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76年获波兰科学院分子和大分子研究中心博士学位,7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78-84年,任波兰科学院助理研究员。84-85年,先后在巴黎大学担任研究助理和客座教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期间,他与我的博士导师Teyssie教授的女儿同在一个课题组工作)。85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化学系任助理教授。98年,被任命为 J.C.华纳自然科学教授。2004年,被任命为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至今,源于ATRP的发明,Kris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之外几乎所有的重大奖项。 3. Mardare D.; and Matyjaszewski K.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of Vinyl Acetate, Macromolecules, 1994, 27, 645-649. 4. 93年年初我开始申请赴美进行博士后研究。第一批信发给了92年来德国美因茨开会的几位我感兴趣的大佬教授,同时Teyssie教授也帮我联系了他认为很不错的美国大学教授和美国公司的研究部门。几位教授相继给我offers:南加州大学(USC)的Hogen-Esch教授(研究方向为阳离子聚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Desimone教授(研究方向为含氟单体在液体CO2中的聚合),Akron大学的Quirk教授(他94年春给我正式发活性自由基聚合研究的offer。此时,我已在办理去美国的各种手续),美国3M研究实验室(研究方向为新型丙烯酸酯聚合物研发)等。我最终选择了老马,主要原因一是老马给我offer早,二是坚信活性自由基聚合是未来。当时非常不解的是,Teyssie教授不支持我投奔老马,一直不给我写推荐信。但我那时就想去老马那儿。老马也很善解人意,告诉我,尽管原则上需要导师Teyssie的推荐信,但他可以想方法帮我搞定。 5. 杜邦Marshall实验室(DuPont Marshall Laboratory)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南部,建于1917年,属于杜邦汽车部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部门。2009年6月,杜邦关闭了这个具有80多年历史的研究所。 6. Marshall Lab终身研究员Fryd博士在活性自由基领域颇有建树,是业内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他参与了澳大利亚小组RAFT(Reversible Addition-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 Polymerization,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聚合)的研究【6a-b】和其他种类活性自由基聚合的开发【6c】。(a) Krstina,J.; Moad,G.; Rizzardo,E.; Winzor,C.L; Berge,C.T.; and Fryd, M. Narrow polydispersity block copolymers by free-radical polymeriz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macromonomers; Macromolecules, 1995, 28, 5381–5385;(b) Krstina, J.; Winzor, C.L; Moad, G.; Rizzardo, E.; Berge, C.T.; Fryd, M. A new form of controlled growth 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 Macromol. Symp., 1996, 111, 13–23; (c) Wayland, B. B.; Poszmik, G.; Mukerjee, S. L.; and Fryd, M.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of acrylates by organocobalt porphyrin complexes. J. Am. Chem. Soc., 1994,116,7943-7944. 7. 第一次见老马是92年7月在德国美因茨那次“阴离子聚合及相关聚合反应”研讨会上。虽然那天没太注意他的报告(偏重于活性聚合动力学模拟仿真),但他是第二天下午发生“美因茨”碰撞的GTP session的主席,会后我主动向他打听有没有博士后研究的职位。93年7月在保加利亚度假圣地伯来维滋(Borovets)召开的一次IUPAC国际会议上(Th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tionic Polymerization and Related Ionic Processes; Borovets, Bulgaria; July 5-8, 1993)第二次遇见他。想必是我的口头报告打动了他,休息时,他找到我,给了我offer。去美前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比利时Gent大学,时间在94年7、8月。我专程去Gent听了他在Goethals教授实验室做的报告,并确认了去他实验室的具体时间。 8. Matyjaszewski, K. Ranking Living Systems, Macromolecules, 1993, 26, 1787-1788. 9. 老马和Scott研究的degenerative transfer polymerization与我设想的自由基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ATRP)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定义它们的角度不一样罢了。我还是认为ATRP更能表达其聚合反应本质:radical species(自由基活性种)和atom transfer pathway(原子转移路径)。但是,我到老马实验后不久,在一次小组会上建议用ATRP代替degenerative transfer polymerization时,遭到老马的断然否决。后来,Scott告诉过我,他们没有读过Curran的文章,也不知道相关的小分子原子转移自由基加成反应。我一直好奇,那他们是如何想到退化转移聚合的?我问Scott,他含糊其辞。 10. (a) Matyjaszewski, K.; Gaynor,S.G; and Wang, J.S. 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s: the use of alkyl iodides in degenerative transfer, Macromolecules, 1995, 28, 2093–2095. (b) Gaynor, S.G.; Wang, J.S.; and Matyjaszewski, K. 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 by degenerative transfer: eff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ransfer agent, Macromolecules, 1995, 28, 8051–8056. 11. Hertler, W. R. ;Sogah, D. Y. ; Webster, O. W. ; and Trost, B. M. Group-transfer polymerization. 3. Lewis acid catalysis, Macromolecules, 1984, 17, 1415–1417. 12. Udding, J.H.; Tuijp, C.J.M.; van Zanden, M.N.A.; Hiemstra, H.; and Speckamp, W.N. Transition metal-catalysed chlorine transfer radical cyclizations of 2-(3-alken-1- oxy)-2-chloroacetates; formal total synthesis of avenaciolide and isoavenaciolide”, J. Org. Chem., 1994, 59, 1993-2003. 13. Wang, J.S.; and Matyjaszewski, K. Controlled/"Living"radical polymerization.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ition-metal complexes. J. Am. Chem. Soc., 1995, 117, 5614-5615. 14. (a) Wang, J.S.; Bayard, Ph.; Jerome, R.; Varshney, S.; and Teyssie, Ph. Macromolecules, 1994, 27, 4890-4895;(b) Wang, J.S.; Jerome, R.; and Teyssie, Ph. Macromolecules, 1994, 27, 4896-4901;(c) Wang, J.S.; Jerome, R.; and Teyssie, Ph. Macromolecules, 1994, 27, 4902-4907;(d) Wang, J.S.; Jerome, R.; Bayard, Ph.; and Teyssie, Ph. Macromolecules, 1994, 27, 4908-4913. 15. (a) Wang, J.S.; and Matyjaszewski, K. Controlled/"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halogen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promoted by a Cu(I)/Cu(II) redox process, Macromolecules, 1995, 28,7901-7910;(b) "Living"/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 transition-metal-catalyzed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 conventional radical initiator, Macromolecules, 1995, 28, 7572–7573. 16. Lodge, T. P. 40 Years of Macromolecules, Macromolecules, 2007, 40, 1-2. 17. Beers, K. L. The first dive into the mechanism and kinetics of ATRP, Macromolecules, 2020, 53, 1115-1118. 18. Lodge,T. P. Celebrating 50 Years of Macromolecules, Macromolecules, 2017, 50, 9525–9527. 19. Moad, G. Living and controlled reversible-activation polymerization (RAP) on the way to reversible deactivation radical polymerization (RDRP) (mini-review), Polym. Int., 2023, 72, 861–868. 20. Gomollón-Bel,F. Ten chemical innovations that will change our world: IUPAC identifies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chemistry with potential to make our planet more sustainable. Chem. Int., 2019, DOI:10.1515/ci-2019-0203. 21. Kato, M;Kamigaito, M;Sawamoto, M;and Higashimura,T. Polymerization of methyl methacrylate with the carbon tetrachloride/dichlorotris (triphenylphosphine)ruthenium(ii)/methylaluminum bis(2,6-di-tert-butylphenoxide) initiating system: possibility of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Macromolecules, 1995, 28, 1721–1723. 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om_transfer_radical_polymerization 23. Ouchi, M. and Sawamoto, M. 50th Anniversary perspective: metal-catalyzed livin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discovery and perspective, Macromolecules, 2017, 50, 2603–2614.
附件一
京都大学Sawamoto教授团队发现的金属催化活性自由基聚合
前已叙述,日本京都大学Sawamoto教授团队于1995年早于我们独立发表了一篇金属催化的甲基丙烯酸甲酯活性自由基聚合的通讯文章(图11)[21]。其实,在这篇通讯文章中,Sawamoto教授团队提出的金属催化活性自由基聚合机理与我们提出的金属催化ATRP机理完全相同。 ATRP发现之前的十多年,Sawamoto教授团队是乙烯基醚类单体活性阳离子聚合研究的先驱和领袖,取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就。在上述他们发表的第一篇活性自由基聚合通讯文章中[22],Sawamoto教授明确指出,效仿他们开发的乙烯基醚单体活性阳离子的引发催化体系,他们设计和尝试了相似的R-X(X=Cl)/金属络合物体系应用于活性自由基聚合(图11)。在另一篇综述文章中[23],Sawamoto教授更清晰地图示了他们的金属催化活性自由基聚合理念直接来自于他们致力研究的活性阳离子聚合产生的灵感(图12)。
图11. ATRP发明人之一、日本京都大学Sawamoto教授团队发表的第一篇活性自由基聚合文章。文中,他们明确阐述了其活性自由基聚合概念的产生源于他们已深刻研究的乙烯基醚单体活性阳离子聚合(橙色标记部分)。其实,Sawamoto团队报道的金属催化的活性自由基聚合就是金属催化的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RP) 图12. ATRP发明人之一、日本京都大学Sawamoto教授团队在这篇综述文章[23]中清晰图示了他们的金属催化活性自由基聚合(也即ATRP)理念直接来自于他们致力研究的活性阳离子聚合产生的灵感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