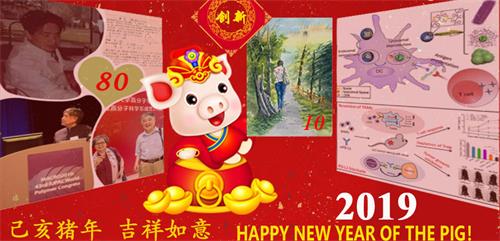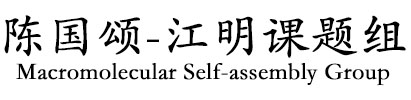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我的院士“导师团”:“一土二洋三大牛” 我的院士“导师团”:“一土二洋三大牛”
苏 璐
去年 10 月份回国探望江老师和师母。老师提及正在筹办一个公众号,旨在分享探讨科学背后的故事。并饶有兴致地拿出两条几乎一模一样的领带,娓娓讲出一个属于他,也属于当初中国两代高分子学人的“领带情结”(图 1)。仅月余,我便在《旦苑晨钟》公众号上读到了更多动人的细节(《我学术生涯里的领带情结》,本公众号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发文)。《旦苑晨钟》现已引起广泛关注,篇篇文章如阵阵晨钟,余音绕梁,响在耳边,钻入心底,引起了我们心灵的共鸣。想想自己的科研路,我是何其幸运,在攻读博士和两站博士后期间,先后拜得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荷兰科学院院士三位院士导师,此等经历为朋友所羡慕。不写点文章对不起三位“大牛”。小编郭明雨师兄为我文章取名:“一土二洋三大牛”。
“一土”: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明
说到“一土”,就不得不感叹人生的奇妙——我与科研竟缘起于一篇名为《从高分子相容性到大分子自组装——一个科研攀登者的感言》的文章(图 2)。多年前,在西北工业大学读大三的我,无意中点开了这份文稿,读着读着竟莫名地哭了。舍友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忙过来安慰,我却转头定定地对她说:“我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研究生导师是谁了!”接着赶紧给她看了文章作者——复旦大学江明院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实验室做实验时的照片,他就是我要讲的“一土”。按小编师兄的说法,“土”是因为 1938 年出生于扬州的江先生是名副其实土生土长的、本土培养的科学家,没有读过硕士、博士,甚至本科都是在大学三年级就提前毕业了,所以先生经常自嘲为“大专生”;后历经磨难,41岁科研才得以起步,1981年访学归国后的每篇研究论文、每项研究成果都盖着本土复旦印,署着本土中国籍。立足国内奋斗数十载,67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读过江先生《我学术生涯里的领带情结》一文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位“土院士”不但不土,还相当“前卫”,在很多方面更是非常“时尚”,这一点留给小编师兄以后写吧。
图1. 2023 年 10 月拜访江老师和师母。江先生手持他的“传家宝”:相隔四十多年的两条会议领带,深情讲述其背后的精彩故事
图2. 江老师在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研究生论坛上的演讲文稿(科学, 2007, 59 (1) , 5-9)
不过,当初立志拜入江老师门下,好事却是多磨。大三临近结束时,身为年级总评第一的我怀着对科研的一片憧憬,踌躇满志地通过邮件联系了江老师,表达了想要保送他名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意向。几天后,收到江老师的回复邮件,表示欢迎加入他课题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心情异常舒畅,做梦都想笑的那种。奈何后来学校政策突然有变,为了留住“人才”,学院前三名不建议向外校保送。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无奈之下,只得发邮件告知江老师。江老师很快回复,且给我留了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并嘱我可随时打电话给他。当时我正在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做实习项目,心神不定。犹豫很久,终于在一天晚上拨通了江老师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像一个年轻人,我有些迟疑,说到:“您好,您的声音听着很年轻,我找江老师”。那个年轻的声音回复道:“我就是江明,你们这些孩子就会哄我开心。你保送遇到困难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也不要不开心。”继续安慰我说:“万一保送不成功,也可以考过来,正好趁机系统巩固下基础知识......”电话挂断后,我坦然了许多。是啊,不过是再考一场,又有何难?实习结束返校后,我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拿着外保申请单在院办和校办之间走了几个来回。可惜不但没得到签字批准,连申请单也被院办扣留了。怀揣希冀而去,满怀失望而归。第二天中午,我正躺在床上给自己做“考研心理动员大会”,并盘算着怎么和江老师说我这边的坏消息。不料,先生竟打来电话:“我给你们张院长打过电话了,她应该很快就会通知你,你可以外保了......”。挂断电话后,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还没来得及反应,院办电话就来了,通知我去领签了字的外保申请书。我一路跑,一路笑,到院办拿到申请书后,又一路跑,一路哭,最后干脆跑去启翔湖边,放声大哭,方觉畅意。后来我不禁暗叹,那晚和江老师通话,先生只是安慰鼓励我,却丝毫没有提及会亲自帮我联系学校“放行”。就这样,如坐过山车般,我被江老师捞去了复旦。 事后才了解到,当时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的张秋禹院长在接到素未谋面的江老师的“求救”电话后,深受感动,特批放行。自此以后,校院领导经过多次讨论协调,理学院改变了政策,再也没有为难过那些想要去外面看看的孩子们了。江老师为我们开了一扇通向更高科研机构的窗!前段时间小编师兄得知此事后告诉我,据他所知,先生一向(尤其是当选院士后)反对“走后门”行为。所以说我应是先生几十年科研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因“爱才心切”而破例“走后门”求得的学生。 话说回来,虽然之前有过邮件、电话联系,但第一次见江老师,还是在 2008 年初秋的保送面试。当天上午是和江老师的个人面试,他提问的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什么是玻璃化转变温度,它在聚合物科学中的意义?”以及“你知道三聚氰胺事件吗,作为化学人如何检测?”问题看似简单,既透漏出先生对基本理论的重视,也体现着学者的人文关怀。在了解过我的所谓的“科研经历”后,他又耐心地为我讲解了科学与工艺的差别,当时我懵懂点头,其实直到毕业多年后,才真正解读他当年的话。下午“群面”结束后,江老师递给我一个信封,笑着说道:“复旦高分子欢迎你!”走出跃进楼,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是录取通知书和一等奖学金。复旦,我终于来啦! 一年后,我到复旦报到。很快地,我感受到了老师独有的“老派学究气”。入学后不久,我便因填写博士开题报告被第一次约谈,心中不免打鼓。进入办公室,江老师拿出我的开题报告,上面已多了很多批注,我们迅速地过了一遍修改意见,一切顺利。正当我以为约谈结束时,江老师拿出一张白纸,画了个大大的田字格,提笔写了一个“江”字,为我讲起了汉字的布局美学。我随即沉下心来,重新誊写一版,方才通过。现在大家一律使用电子文档,应再难有这样的逸致和受教机会了。多年后,江老师的字画“千金难求”,真后悔没有好好保存那份先生做了手写批注的纸质版开题报告。 图3. 2009年中秋节,江老师(后排左二)邀请全小组成员在黄浦江边品美食、赏美景
江老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十分活跃,引得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硕士酒井不二(图3,后排右二)慕名前来读博。因此自2009年开始,小组会改用英文交流,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虽然我们准备起来费力了不少,但几年下来英文表达能力大有长进,此后受益匪浅。2012年,江老师和陈国颂老师应邀去英国华威大学参加国际高分子学术大会,该会议设有一个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我和韦孔昌师兄(图3,前排左一)被两位老师选中随同参会。在博士论坛上我也作了报告。当时面对一众英文母语的演说人,心中紧张,但由于在校已有多次组会报告的经历,我尚能从容应对。报告结束时,大概是因为我实验工作做的不错,加上讲得流利清晰吧,坐在后排的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华威大学的David Haddleton(我们习惯称他为“老哈”)教授立刻站起来举手问我:“Do you need a job?”(你需要一份工作吗?),我当时满脸惊愕。但看看老哈一脸真诚,又看看早已笑开花的江老师和陈老师,我立刻明白这是“大牛”对我的赞许,心中甚是甜蜜。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会议对我们一行四人来说都意义非凡。这是江老师最后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应邀做大会邀请报告(图4),也算是他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完美谢幕吧!陈国颂老师也有一个报告,是她回国工作后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也是她后续辉煌科研生涯的精彩揭幕战。对于我和韦孔昌师兄来说更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讲坛! 图4. 2012年7月,江老师在英国华威大学MacroGroup U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ymer Synthesis上做大会邀请报告
除了英文表达带来的小小焦虑,组会则是我们学生们最期待的。因为那既是我们相互交流、解决实验难题、分享成功喜悦的时间,更是江老师的“故事会”时间。江老师总能对大家报告的工作或文献做出精妙的科学点评。学生讲到某位大牛的论文,总会引出江老师讲该大牛或论文背后的精彩故事,时而穿插些小八卦,让人听来津津有味。我时常想,为什么江老师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且故事里的每个人都那样栩栩如生?后来读了江老师写的科学史小记,我才明白,即使在那十年的至暗时刻,他都从未放弃希望,黑暗中瞬息即逝的一丝火光,对他而言都是满满的希冀,那么后来这些大大小小的美好瞬间,又岂能不印入脑海,不鲜活跳动? 我到复旦读博时正值江老师科研生涯的最后一次“华丽转身”。为拓展研究方向,他于2008年底引进陈国颂老师。当时年轻的陈老师在美国做博士后,既无大把牛文,也无辉煌研究经历,要进名校院士的课题组并无把握。她糖化学研究背景和隔洋交流时表现出的研究热情深深打动了江老师,先生果断邀她作为讲师加盟。事实证明,江老师确能慧眼识珠;陈老师也未负先生厚望,带着对糖化学的满腔热情,在自组装领域开辟了甜蜜的新天地。而我有幸成为组里糖化学和自组装交叉领域的第一名“先锋”,得到了两位老师的精心培育。因此每次报告,言必称甜蜜,但这份甜蜜属实来之不易。博士四年级时,课题组大组会上(图5)我有幸拿到了课题组内的SAGA(Self-Assembly Group Award)大奖。江老师问我:“你做了那么多含糖聚合物,有没有一种糖可以表达你读博的感受?”我顿时语塞。江老师微微一笑,说到:“我想应是‘老姜糖’,初尝辛辣,但最终归于甜蜜。”事实证明,“江”(姜)确实是老的辣,这份甜蜜果然后劲十足,五年的系统科学训练,为我之后的科研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5. 2012年,第八届JCY(江明-陈道勇-姚萍)联合课题组大组会。每个小课题组选一名同学介绍自己的实验进展作“大会报告”,且会邀请已毕业的优秀组友作“特邀报告”,最后颁发SAGA大奖。前排左起:陈国颂教授、江明教授、姚萍教授、陈道勇教授;第三排右起:酒井不二、苏璐、韦孔昌都笑得十分灿烂
时间很快到了博士最后一年,大家陆陆续续开始找工作,而我却忙于寻找自己,总觉得科研还未开悟。有一天,江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以后的打算。我说,或许出国做个博后继续开化吧。就像算准了一般,他问道:“那你想去Karen Wooley[1](卡伦·伍利)(图6)教授课题组吗?你邹炯师兄在那里做得很好,马上要离站了。Karen近日问我有无合适博后人选,我想你适合。”我连称“想,想,特别想。”就这样,先生五年前为我“折腰”,亲自向素未谋面的院领导打电话,捞我来到复旦;五年后又为我敲开了“二洋”导师之一的国际知名教授Karen Wooley院士课题组的大门。毕业离开复旦那天,江老师赠予我一个精美的陶瓷水杯,嘱咐我走出国门要自信,落落大方,代表中国形象,并鼓励我抓住每一次学习的机会,系统提升自己。送我到他办公室门口时,笑着对我说:“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转身,我的眼泪脱眶而出。后来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当我感到怯弱无力时,总会想起老师的叮咛,大胆地往前走!
[1] Karen L. Wooley,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教授,高分子材料化学家。曾任JACS副主编、执行主编(2014-2022年)。
图6. Karen教授(前排怀抱小狗的女士)课题组圣诞聚餐合影(2016年)
“二洋”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 Karen Wooley
对Karen教授,我是久闻大名。第一次见面是201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当时并不知日后还有此等机缘,初次相见,未敢贸然向前交流,即已留下深刻印象:她一头金色秀发,身着短裙,踏着凉拖,激情澎湃地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我的第二站博后导师E. W. (Bert)Meijer教授(人称“波特”)还曾与我八卦,说Karen年轻时很时尚,宛若影星。 来到Karen组时,邹炯师兄已经离开,但给我留下他的一众嫡系中国师弟(Karen很喜欢中国学生,至今培养的中国博士、博士后有40多人)。他们对我适应美国生活和Karen课题组文化帮助巨大,同时也向我讲述了很多Karen的传奇往事。例如她读博时,上午还在实验室做实验,下午羊水破了,去医院紧急生了个孩子,第二天出院又跑回实验室继续做实验,随即被导师Fréchet [2] 老爷子“骂”回了家。之后又生了老二,助理教授期间生了老三。连生三胎,期间科研产出却更胜一筹。所以博士毕业后,直接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拿到教职,六年后升任正教授。若有什么遗憾,那或许是三胎都是儿子,所以她特别稀罕女孩,这亦或是她致力于培养女性科学家的动力来源之一吧。
[2] Jean M. J. Fréchet,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家,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副校长。
我对Karen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典型的“双标”人生:对自己要求近乎苛刻,是整个课题组最勤奋的一个,日程甚至精确到分钟;对学生则是呵护有加,稍微有点小成就,她就会夸赞我们“Great job! Well done!”(了不起的工作!干的好!)(图7)。不仅有精神上的认可,更有真金白银的支持。在美国,博士生做助教(teaching assistant,TA)用以减免学费是常事,可她却为了学生能够专注于科学研究,坚持不让学生去做TA,并为每个学生支付高昂的学费。这是很少见的。即使经费吃紧时,她仍明确承诺宁可缩小课题组规模,也绝不让学生去做TA。如今我自己独立成立了课题组,才更明白这份承诺的份量。 图7. Karen教授(前排中)在实验室与博士研究生讨论工作,同学们喜笑颜开
第二个深刻的印象便是她独特的手把手论文修改模式。准备发表文章时,Karen会让文章的主要作者们坐在身边,首先询问想投哪个期刊——学生们的提议她一般都会同意,除了《美国化学会志》(JACS),这个后面解释。接下来她会打开稿件文档(包括支撑信息),逐字修改,小到一个斜体字、一个空格,大到逻辑结构、语法句式,她都会仔细检查,指出问题,并且现场修改。她对文章的遣词造句也很考究,会一边改,一边细心地向学生们解释原因。看她改论文,我才第一次感受到英语的美,怎一个享受了得。当然,有时她会突然对文章和实验的细节发问,如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她便秒变严肃,提出批评与建议。所以,每次修改论文之前,我都有些坐立不安,会抓紧一切时间做足功课,生怕出纰漏。虽庆幸她从未对我突然疾言厉色,但即使如此,如今想到这个过程,我的心跳都会不自觉加速。一般一篇文章,经她这么改个两三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投稿了。不仅效率高,学生还能学习到她的逻辑思维和写作技巧,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棒的论文写作教学模式。现在我也在尝试同样的教学方法,奈何囿于英语水平有限,至今功效甚微,但这依旧是我奋斗的目标。 为何投稿JACS如此慎重?这说来也是一件趣事。2014年Karen当选为JACS副主编。众所周知,JACS在化学期刊界的地位当属龙头老大,因此她的当选本是好事一件。可谁承想Karen也因此主动提高了自己课题组工作投稿JACS的门槛,从前组里每年总能发表两三篇JACS,可自她任副主编直至卸任的九年时间里,组内一共投稿八篇,其中还包括一篇与其他组的合作论文(本组同学非一作)。算来,平均一年不到一篇的产量,与之前差别巨大。我很幸运,在这期间成功发表了两篇JACS。第一篇论文经过了多次讨论与反复完善,才获得了Karen的同意。第二篇工作则是基于一个偶然发现,Karen很喜欢其中简洁精巧的化学设计,因此文章还未动笔,她竟主动推荐我们投稿JACS,令我喜出望外。在任职JACS的第九年(2022年),为了能够更多地陪伴家人,Karen主动卸任了执行主编(executive editor)的位置,如此魄力和风格,真真让人称赞。不知组内同学有无私下庆祝,毕竟2023年课题组JACS发表数量又陡增至2篇。 此外,一般博士后常签1-2年的短期合同,在导师经费吃紧时拎包走人也属实常见,所以总不会有太多安全感。庆幸的是,Karen在第一次考评会时便对我说:“你可以一直安心留在组里工作,当有更好的机会时,可以随时离开。”就这样,我安心又放肆地做着科研,好不快活。时光流转,两年后的又一次考评会,因为家庭原因,我提出想要寻求去荷兰发展的机会。她没有丝毫犹豫,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询问有无中意的合作导师,她乐意推荐。而我对荷兰化学界的了解,也源于江老师的故事会。他曾对我们表露出对埃因霍温理工大学Bert Meijer [3](图8) 教授的欣赏,甚至说他是“老板之星”。曾推荐郭明雨师兄前往做博后,深受Bert喜爱,因此我很向往在Bert教授课题组做第二站博士后。Karen听说是Bert,会心一笑。不知是不是天意,Bert在两月后访问Karen课题组,Karen特意安排我与Bert会谈,聊了半小时,便异常顺利地拿到了去他课题组做博士后的口头offer(同意)。后来我才得知,这次的“异常顺利”得益于Karen的强力推荐。就这样,我提前终止了在Karen课题组的合同,开启了在另一“洋”导师Bert Meijer教授课题组的科研生涯。
[3] E. W. (Bert) Meijer,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教授,超分子化学家。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图8. 2023年5月于瑞士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合照,此时我已入职莱顿大学一年有余。左起:Bert Meijer教授、苏璐、陈国颂教授
“二洋”之二:荷兰科学院院士 Bert Meijer
Bert于我而言,既是导师,也似父亲。和很多大牛不同,他总有大把的时间和学生讨论工作,或三两人,或一对一,总能快速高效地解决学生在科研上的困惑。而且他没有漂亮的话术,却能用简单的几句话直击你的心灵,在这背后,是他强大的同理心。 由于疫情和一些个人原因,我在Bert组工作了四年半,因此常常有同事调侃,说我在这里又读了个博士(荷兰博士4年)。在这期间,我事业上最大的收获便是提升了科研品味。当然,除去科研,还有太多的故事和情愫,此处我想简单聊几个小故事。 Bert是个十足的绅士。第一次和他用餐是在美国德州,我和A助理教授陪餐。由于是午餐,我和A随意点了汉堡,接着直接拿起来大快朵颐;与此同时,Bert却铺好餐巾,拿起刀叉,很优雅地享用起来。我和A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地放下手中汉堡,随即也拿起刀叉,十分拘谨地吃起来。多年以后,又一次一起用餐,我和Bert提起此事,他哈哈大笑,随即拿起刀叉,耐心为我讲解了西餐文化。 2020-2021年我怀孕期间,因为疫情,家人不能按计划赶来照顾。他很快觉察到我的焦虑,对我说:“别怕,你可以的,我也在。”此后,他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办公室聊天,他站着,我坐着,时而聊聊科研,时而谈谈人生。他还常常与我分享刚出生的孙女的照片和视频,为我减轻临近生产的焦虑。有一次,我在另一栋楼做测试,做完正准备离开时,迎面看到他向我走来,说正到处找我。我俩坐在咖啡角,就这样从科研到人生,聊了一个小时。后来我想,或许他只是想确认我状态是否还好。在此期间,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发现,和之前的自然认知截然相反。他知道我好奇心重,必对此穷追不舍,为了让我少进实验室,他交代其他学生配合我的工作。最终我们成立了一个“梦之队”(图9和图10),把问题研究透了,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上[4]。后来有多家媒体采访我相关的工作,我总说这是团队的功劳,自己只是幸运。别人会说我谦虚了,岂知实乃肺腑之言。值得一提的是,休产假前,我们的工作正处于最后攻坚阶段,可他特意嘱咐,要我两个月内不要打开电脑,健康才是头等大事,其它都可暂缓。
[4] Su L., Mosquera J., Mabesoone M.F.J., Schoenmakers S.M.C., Muller C., Vleugels M.E.J., Dhiman S., Wijker S., Palmans A.R.A. and Meijer E.W., Dilution-induced gel-sol-gel-sol transitions by competitive supramolecular pathways in water, Science 2022, 377, 213-218.
图9. 2020年疫情期间,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Helix大楼内,地上可见黄色警界线、蓝色指示牌。左图照片中心展示的是我指导的硕士Bart van den Bersselaar(左图右上插图)赠予的BTA分子(化学结构式如右图所示)编织模型。我在Meijer课题组四年半时间,都在研究这个分子 图10. “梦之队”成员Sandra Schoenmakers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场(左图,Bert教授正在为Sandra授予博士学位),我和刚满半岁的女儿也应邀线上出席(右图)
2021年底,我提前结束了合同准备回国发展,临近回国前几日,原拟聘用单位情况有变,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通过邮件向Bert说明了情况,他马上约我面谈,但地点约在了校外,而非他的办公室。后来方知,他是怕我回学校见到同事尴尬。确认我心意后,他马上给了我新的合同,且再三嘱咐全组同学,见到我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又回来了。与此同时,他又联系了莱顿(Leiden)大学,推荐我去那里做助理教授。自始至终,他不断向我表达,是他太幸运了,可以继续和我一起做研究,而他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要我千万不要有任何压力。
在2019年庆祝Bert教授 65岁生日的聚会上(图11),他培养的众多博士和博士后纷纷前来祝贺,天下桃李,齐聚一堂。Bert端着酒杯站在高处,讲到了他的梦想就是努力帮助我们实现梦想。至今,Bert已经培养了100多名博士和众多博士后[5],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或大型公司的研发人员和高管,在总人口仅约1600万的荷兰这样的小国,这是极为罕见的。大家举杯相庆时,我悄悄抹去眼泪。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异国他乡漂泊不定的求学游子来说,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慈父般的导师,感觉一切就像做梦一般,美好得不真实。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导师,时而还会产生困惑。每当这时,我就会坐上从莱顿到埃因霍温的火车,敲开他的办公室。而在返程的火车上,我的眼神便会坚定,耳边回响着教授的话,“专注于你能改变的,讲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个学生,莫问前程。”
[5] The power of Bert Meijer - supervisor of more than a hundred PhD’s (https://www.tue.nl/en/news-and-events/news-overview/21-12-2023-the-power-of-bert-meijer-supervisor-of-more-than-a-hundred-phds )
最后,正如小编师兄在王健君教授《得遇良师,受教终生》一文的导语中所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然,‘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回顾自己的科研路,何其幸哉,前后得遇“一土二洋”三大名师接力助推。时至今日,每当我产生自我怀疑时,他们仍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温暖的双手推我一把,让我顿时拨云见日,他们却从不求任何回报,我想这就是“导师”这个职业的属性之一吧。现在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尽己所能地伸出双手,深耕教育,助力科学,做好传承。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公众号《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