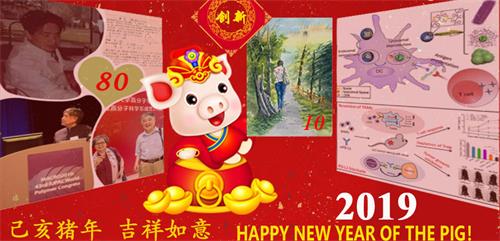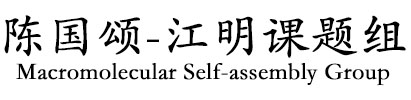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自愿封控、闭门思研” 107天 “自愿封控、闭门思研” 107天
丁建东
2024年5月4日
新冠疫情在我国通过2022年底的突然放开而迅速平息了,三年疫情和封控留给人们的影响正在逐渐淡去。近日江明院士三次邀请我写一篇有关科学文化的小文,供其倡议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向同仁分享。最后一次直接以“封控中的学术痴迷”为题提出了要求,并激励我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经历。古今中外能有这个‘绝对闭门思研’机会且有所得者,太少,不记下来何其可惜?”。我知道这次是难以推托了,也对先生的器重甚为感激!便利用2024年五一长假的机会,在疫情过后的第二个五四青年节完成了江先生交待的命题作文。 遥想疫情封控,真是恍若隔世!2022年上海事实上“封城”三月,一开始是浦东和浦西“鸳鸯封”,但是浦东的核酸全员检测结果十分严峻,上海市便加大了封控力度。作为高等院校自然首当其冲。复旦大学由于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在“封城”之前已提前收紧,因此,我的“留守”时间长于三个月。
为守护“国重”自愿被封
非上海籍的学生是校园封控的主要人群。教职员工们纷纷“居家办公”,干部们则被要求轮流值守。我虽然担任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简称“国重”)的主任,但本国重提前“去行政化”了,我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故无留守义务。但是,考虑到偌大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需要有人守护,并且还有不少研究生在做实验,留守的教师不宜太少,我就自愿“居校办公”。我多年来习惯了在办公室而非家里处理教学科研管理事务,一旦脱离了工作的“微环境”,尤其是台式电脑,效率必然大打折扣。幸好家里并无特殊情况,太太和孩子也予以理解,我就以校园为家了。未曾想这一封就是107天! 学校和系里组织了一批物资,包括被褥、少量行军床等,我也基本没有去领,将物资留给了更加需要的师生们,因为我原本就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配有三人沙发,俨然已属封控中的“土豪”。由于抗疫的原因,我竟养成了在办公室囤积物资的习惯,至今仍然如此,不知道这会不会演变为一种“癖好”。 生活上的不便还是很快显现出来!某天一位食堂员工成为密切接触者,所有的食品都不能发出,我和其他被封师生挨了一个上午的饿。不过总的说来,学校已是非常尽力,安排自愿者将一日三餐送到办公室门口。吃的问题解决了,但没有地方洗澡。幸好,我们高分子系之前已在大楼的每个厕所里安装了电加热装置,原本是为了大家冬天洗手不感到水凉,现在竟成了擦洗身体的绝好水源。 本来说封几天,也就没有做充足的准备,但最终却超过了三个月,换身衣服已成为极大的奢望。我每天晚上躲进走廊的公共厕所,关上门(好在当时人已不太多),“洗澡”后在里面洗衣服,然后披上外套匆匆溜回办公室,再用电吹风进行可称为干燥的实验操作。过了一段时间,毛巾和内衣等俨然已回到了解放前。终于有一天,学校给每位留守的教师发了一包生活必需品,打开一看,欣喜万分,如久旱遇甘霖,禁不住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援军’到了。在江湾校区办公室因疫情被封一个多月后,那个有沧桑感的手巾与那双自发成洞的袜子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不过这段日子科研工作还真的没耽误,并且在宁静的化学高分子楼里的一盏孤灯下有时还蛮有效率。愿天下太平,岁月静好。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并配发了自嘲性质的图片,除了那条千疮百孔的毛巾以外,还夹带展示了几个刚用完的新冠抗原试剂盒(自然只能有一道杠):
微信朋友圈发出后,得到了各方的点评和关心,倍感温暖。我之所以在收到这包东西之前不发朋友圈,是不想增加领导负担。当时微信朋友圈充斥着各类不满和焦虑,包括领导在内的各个阶层活得都不容易。是日为公元2022年4月25日。从此之后,我得到了院系和学校更多的关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我予以了关照,对此至今心存感激! 后来,复旦大学启用了体育馆中游泳馆的淋浴设备,并安排被封的师生员工 “错峰洗澡”。第一次不是在厕所非典型性洗澡,竟成为一种莫大的享受。这样的幸福感怎能不与大家分享?我在淋浴后用手机拍摄了这幅照片:
并配发了朋友圈,文字如下: “自愿封闭在办公室二月有余,其间一日三餐送至门口,背部细胞也早已自适应了沙发的stiffness,只是洗浴有所不便。今晚承蒙学校安排至游泳馆错峰洗澡,一路上同行师生的面庞皆洋溢着节日的光彩。我蓦然想起少年时阅读的小说‘新浴’,介绍了一个村的人们首次集体沐浴的喜悦。论语云:‘子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想必孔子等古来圣贤即重沐浴,何况疫情中的我们乎?今晚江湾游泳馆的灯火,不是光明,而是希望!故,发朋友圈以记载这个历史时刻。壬寅新冠,于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是日为公元2022年5月22日。
疫情三年出了三部书
疫情三年对科学实验带来了诸多不变,但“闭门思研”文案工作效率甚高。我在这三年出了三本书,分别为《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上)》、《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下)》、《生物材料表界面与表面改性》,均于疫情最后一年(2022年)上半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第三本书的全部清样校对工作均在自愿被封期间完成。我自己直接撰写了好几章,还邀请了若干学术活跃的专家写作各自最为擅长的部分,这些章节的清样先由他们各自负责,然后我复核了全部章节,找出了不少遗留的问题。例如:我发现有两章在介绍同一个重要的开创性事件时年份不一致,就分别与各章的负责教授微信电话讨论,认为各自都有道理。我随后上网仔细查阅,建议了各自更为合理且内容一致但文字不雷同的表述,并得到了两位教授的认可。非常感谢同行专家们的配合! 疫情催生了大家使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除了网络教学和网上组会以外,还进行了多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网络答辩。“闭门思研”并不妨碍借助网络“开门办学”。有一天接到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联合会前主席、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Peppas教授的电邮,热情推荐我为iCanX系列学术讲座做个报告,不久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张教授的正式邀请。上网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个民间的系列讲座,颇有活力,便欣然应允。最终被安排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陈刚教授同日报告。当时全世界人民的心情都不好,各类宣泄情绪充斥网络,能有一个机会面向全球用英文讲解科学,也是一种荣幸和责任。我认真准备了报告,并提前一天在朋友圈中作了预告: “疫情封闭之际,应邀于本周五晚北京时间20:00为海内外科技工作者和爱好者作英文报告Biomaterial Microenvironment & Tissue Regeneration(细胞的材料微环境与组织修复再生)。这个由北大教授和海外教授民间组织的公益性iCanX网络平台充满活力,免费为大家提供各个领域的系列讲座,今天(周四)晚上就有好几位报告人,其中两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疫情封闭期间特别需要网上的科技传播,相信科学最终将战胜疫情,并促进人与人、学科与学科、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带来愈发灿烂美好的明天!”
报告日为公元2022年4月29日。
战士听到了冲锋号
疫情期间,如果所工作居住的地方或经过的区域出现了一例阳性或密切接触者,则行程码就被赋“黄码”,从而不能进入校园或者不合适回去。而“次密接”以上的人群则被予以“红码”,要被高度强制隔离。自愿被封校园期间,除了“闭门思研”以外,还思考了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发现按照该法,新冠最多只能算是乙类传染病,法规上只有霍乱和天花被定性为甲类传染病。“强制隔离”仅针对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提升为甲类管理须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方可实施,被隔离的对象应当为“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我没有看到“次密接”的提法,便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反映,接电话的同志态度很好,但最终无果。我十分担忧一直这样封控下去对于经济的打击和学生毕业后就业形势的严峻。一想到这些,心情就不好,也很无奈。 封控期间,测核酸的频率和重要性不亚于一日三餐。后来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可以去食堂打饭,但是要扫场所码。我很快发觉,测核酸的安排严重影响了师生们的工作学习。我向学校相关负责干部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出发点就是,核酸检测的目的是保障有序的教学科研,而不是相反。所幸的是,最终大多得到了采纳。“闭门思研”期间,我也“闭门思国”:中国的层层加码和拷贝走样非常严重,有些时候基层未必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为了维护集体利益,有时需要主动与各级沟通,必要时发出不随大流的声音。
根据疫情期间的主流舆论,除了测核酸以外躺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就是一种“爱国”行为,这等于在鼓励大家“躺平”。我深不以为然,并且担心一旦青年一代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疫情后的局面将很不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复告诫自己绝不能躺平。战士不能轻易离开战场!实际上学校安排了干部等轮换来校园,并非不可以回家;但回来很麻烦,不仅申请获批有一定难度,还一定要先到燕园宾馆隔离几日,而我当时特别不希望中断“战斗”,就一直没有回去,最终成了一位从头到尾、连续不断自愿被封在校园的一线教师。 疫情的次生灾害之一是患有新冠以外疾病的人员得不到及时就医,这个问题在我身上也有一定体现。我患有牙周炎,之前定期去医院看牙,可是疫情当中如果去一趟医院,就被视为新冠“嫌疑”分子,想再回到校园没那么容易。结果牙痛越来越厉害,后来连咬到一粒芝麻都剧烈疼痛。有一天晚上居然由于牙痛而睡不着觉!整个晚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个小时,其它时间连躺着都不行,这是107天中的至暗时刻。当然后来牙痛逐步有所好转,可见人的自愈能力还是很强的,就看能不能坚强地挺过去,当然也因人因病而异。 第二天早上,医务室的门一开我就造访了,这是自2017年底从复旦大学主校区的跃进楼搬到江湾校区的高分子楼之后第一次登医务室的门。值班医生很客气,主动提出她可以安排学校的抗疫用车送我去长海医院、上海九院或某个三甲医院,当然回来她就管不了了,被我婉拒。她开了几个常用西药,但结账时我的校园卡无法支付(大概是我之前多年不进校医务室的缘故),经电话征求领导意见,可以先自付(但有发票)。我这才发现先锋六号等西药的价格显著低于预期,看来国家的药品集中采购发挥了威力。临走前,医生友好地指着门口堆成漂亮造型的药品问我,要不要拿两盒那知名的****胶囊,我笑着摇了摇头。 该日我有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所领衔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将进行结题答辩。这是一个千万量级的国家级大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代表含多个单位的团队向科技部聘请的专家组进行汇报。回到办公室后马上服药,但未见效果。接一个电话时,讲话断断续续,人始终迷迷糊糊。可是,进入网络会议的一刹那,一想到连续五年多我们这个团队的辛劳、一看到网上已有多位匿名的专家和不匿名的本团队骨干,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犹如战士听到了冲锋号,一开讲便全然忘记了牙痛、忘记了疫情、也忘记了无奈。事后一位校外的项目组研究骨干评价,今天的汇报如行云流水,回答问题近乎完美。是日为公元2022年3月21日。 5月20号,我收到了5月17号签发的结题意见。科技部相关管理中心下发的文件指出,复旦大学丁建东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总体执行情况优秀”,且“有效支撑了专项整体目标实现”。
专家组意见特别指出:“开发了具有表面纳米膜的左心耳封堵器等创新产品。获得了中国和欧盟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在国内外进行了大规模示范应用。” 左心耳封堵器用于预防卒中和心肌梗塞。项目最终获得国内第一款左心耳封堵器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并且对于大而不规则的左心耳也适用,取得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成果。所研发的封堵器迄今仍是国内唯一在中国和欧盟同时获证的左心耳封堵器、国际唯一具有纳米涂层以获得适宜细胞响应的左心耳封堵器,已在49个国家和地区临床使用2.5万例,成为一个原创于中国、最终走向世界的生物材料类高端医疗器械。这个工作早在我上一次主持千万量级的国家级项目(作为“973”管理)时就已开始,历经了我们团队十余年连续不断的努力。 这49个国家和地区中,还有少量国家尚未获证、但却被提前使用。这是由于临床试验花费大,公司的产品推广需保持节奏;而一些国家的医生等不及了。有一天,合作公司告知我,经美国医生申请,美国政府破例同意使用,且以医保支付这一在美尚未获证的中国器械,用于封堵大而不规则的左心耳(仅针对已获美国注册证的所有产品均无法解决的病例)。在特朗普总统对华限制的清单中有高端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以严格著称的美国居然为来自中国的一款新型医疗器械开绿灯,着实罕见!我对着公司转来的美国政府的批准函看了一遍又一遍,有那么三秒钟竟然感觉眼眶湿润了。这是十几年前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不枉我们大学、医院和公司多方人员的长期付出!科学无国界,只要具备先进性和不可替代性,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就可以走向世界。上海市政府号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此我深以为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埋头苦干、不懈努力,任重而道远。
自由的花在风中摇曳
疫情期间,网上传闻外滩和南京路长出了草。这个我没有见到,但亲眼见证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园的“大草原”几乎长成了成熟麦田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到这个样子也很不错,整齐划一是一种美,错落有致也是一种美。繁花的出现依赖自由生长的环境。草丛中有时突然出现一丛野花,在风中摇曳,别有一番情调,给封控中的人们增添了一丝生命活力。
头发也随着草一起长长了。在即将离开校园回家的前夜,我在办公室自拍,并回顾了自己历史上的几张留影。当初那个略带青涩的复旦学生和剑桥学子,现在已不再年轻。所幸长发依然浓密,然几根白发悄然出现。 (1999年7月31日,英国剑桥大学)
(2015年11月20日,中国生物材料大会作大会报告)
(2022年6月26日,解除封控前夜自拍于系楼工作室)
终于有一天,根据统一部署,学校通知可以回家了,并且凭借校园卡以及核酸阴性的证明(以随申办的记录为凭)就可以返回校园。关机离开实验室前,我发出了这107天中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消息: “本轮上海新冠疫情,我自愿留下守护学校和国重室107天,今天终于准备回家了!在此期间组织研究生们的线上答辩,撰写和修改多篇学术论文,讨论和规划未来的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草拟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建设方案,合作校对了一部65.8万字的学术专著。校园封闭期间还整理了复旦生物系-复旦材料系-复旦高分子系-剑桥材料系-复旦高分子系的一些个人资料照片(最后一张为封控后期的长发照),回想生物-高分子-生物医药高分子材料的交叉研究历程。成长的足迹、青春的岁月,还有那些年略带青涩的像片!” 是日为公元2022年6月27日。出校门也要刷校园卡。走出江湾校区二号门的一刻,有一种自由放飞的愉悦感。要知道封控期间,抵达校园或者小区门口的外卖最终到自己的手上都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之一。重获自由会倍加珍惜自由。 根据我的生物学知识,只要病毒自己不退却,这个“零”清不了,最终会走向“共存”。同时,基于对大形势的判断,我预料全面放开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最后的结果还是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并且自古以来就有大疫不过三年的说法。一想到此,倍感神清气爽。 不知为何,我竟然想到解封以后,那些在江湾校区草坪自由生长、敢于出头的花草,不久也将被“计划”掉,不由得有点伤感。耳畔响起俄罗斯大文豪普希金的著名诗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那快乐的时光定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是阴沉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瞬息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