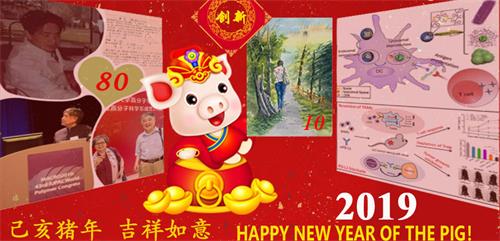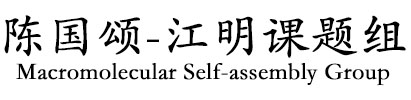 芬兰Jarl B. Rosenholm教授与中国高分子人的情缘 芬兰Jarl B. Rosenholm教授与中国高分子人的情缘
沈青 (东华大学高分子系教授)
Jarl B. Rosenholm(以下简称Rosenholm)教授(图1) 是国内、甚至国外高分子研究领域的许多人不熟悉的人,但他却与中国高分子领域里的好几位学者有较深的情缘。Rosenholm曾是芬兰奥博大学(Abo Akademi University)物理化学系的教授、系主任,在国际胶体化学、表面化学等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他教过的学生和合作者中,有好几位是在中国大学的高分子系里工作的人,其中按时间顺序有我的师兄何平笙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系教授,时为访问学者),师弟刘和文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系教授,时为博士后)和我(东华大学高分子系教授,时为博士研究生)。其实,我也是他指导的46个博士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图1. Jarl B. Rosenholm教授
芬兰奥博大学的物理化学系(图2)是一个建于1921年的老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研究方向很杂。该校高分子系的老主任、曾经的奥博大学校长Bengt Stenlund教授,是这个系毕业的博士(1979)。他也是Rosenholm教授的师兄,还曾经为我赴芬兰留学的资金进行了官方公证(上个世纪80年代办护照时应上海公安部门的要求)。 图2. 奥博大学的校园。物理化学系在图的左上方第二栋白楼的三楼
这里所谓的师兄弟,其实是按我们各自在Rosenholm教授那里做研究的先后时间而定的。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两位师兄弟先后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系的教授,而且还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何平笙教授,1940年11月出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然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他是在1990至1994年在Rosenholm那从事研究的,与Rosenholm 教授一起发表了几篇不错的研究论文。由于重叠时间较短,当时我与何平笙教授不太熟,但他的儿子和女儿那时也都开始在奥博大学读书了,所以这兄妹俩倒是与我在那里不时相见,比较熟悉,那时他们还小。 何平笙教授从芬兰回到中科大后先后出版了《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科学出版社,1994)和《高分子物理实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都是在高分子领域内有影响的著作。他与Rosenholm教授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指导了他的两个中科大的学生,并合作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而与他曾经合作的我的同学J. P. K. Peltonen,现在是奥博大学物理化学系的系主任、教授,还曾经因为与何教授合作发表的1篇JACS的文章,拿到了阿克苏诺贝尔公司那年颁发的小诺贝尔奖。 师弟刘和文是在奥博大学高分子系读的博士,他比我晚到芬兰,他是在博士后阶段跟的Rosenholm教授。 其实,在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系后来的系主任施文芳教授也来到过奥博大学。那时,她刚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奥博大学的高分子系访学。当时,她还到我宿舍聊过天,给了我一本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她回国后,1996年在中科大任教授,后曾任高分子系系主任。 我是1993年11月到芬兰奥博大学的制浆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师从Bruno Lönnberg教授(图3),一个国际制浆造纸领域里的权威。1995年年初我转到物理化学系,开始师从Rosenholm教授。原因是制浆技术系的导师Bruno Lönnberg教授要退休了,也是他让我转系的。我转到物理化学系主要原因是这个系的研究实力强大,科研成果很厉害,仪器设备先进、齐全,让我很是羡慕。 图3. 1997年,我与Bruno Lönnberg教授在加拿大国际会议期间的留影
还记得我与Rosenholm教授的第一次面对面聊转系的事,他看了我的简历后说“你可以来我们物理化学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是做我安排的项目,可以立即给你资助;二是你自己选择做你喜欢的项目,然后我根据你的研究成果为你申请政府项目资助。”我略为思考了一下说 “我还是按您的第二方案,做我自己喜欢的项目吧。”因为我知道,物理化学的研究包罗万象,有研究量子力学的,有研究无机材料的,也有研究高分子的等等。 因为Rosenholm教授对我的彻底放松管理,于是,我可以利用在制浆技术系做了整整一年的实验所获得的样品和数据,再根据物理化学系拥有的强大仪器优势(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几乎是同步拥有NMR-共享、XPS-共享、AFM、拉曼光谱等高端仪器),设计我的研究体系,以解决当时国际制浆造纸行业内的一些未知科学问题。 物理化学系对博士学位的要求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至少三篇学术论文,40学分一篇,记120学分。而发表国际会议论文一篇,记1个学分。此外,还需要在本系获得25个课程学分(可以包括发表国际会议论文的1个学分)和外系获得15个相关课程学分。这种课程设计是学校为了防止本系老师和学生的作弊而设计的硬性规定。 师从Rosenholm教授后,我开始逐渐了解和熟悉他。而他也开始从我的研究及给我上课的过程中了解我。我到物理化学系的第一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篇论文的实验及初稿,题目是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木材的湿润性。当我把论文交到Rosenholm教授手上时,他表扬了我的进度,然后让教我做实验的师兄初改我的论文。可是,这位师兄正面临毕业,忙着找工作,所以由他负责改稿就惨了,不断地拖。然后是一稿又一稿地改,最后再是Rosenholm教授又改了几稿。后来我才知道,其实Rosenholm教授是不愿意让我早发论文,早毕业。虽然这篇论文的修改时间超长,但投稿还算顺利,直接投了德国的Holzforschung(图4),是国际上木材研究领域最好的期刊之一。有意思的是,在这篇论文[1]修稿期间,有一天,突然有个电话打到办公室找我。当我听到对方的自我介绍时,着实吓了一跳!他是当时的Holzforschung的主编,德国一个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在电话中问了我一些问题,讨论了我的论文,这是我发表不少论文中碰到的唯一一例:主编来电、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探讨论文的内容,比博士论文答辩时问的问题还仔细。 图4. Holzforschung期刊封面
这篇文章有好几个审稿人,虽然是匿名审稿的,但其中一个审稿人的意见是让我去读Wettability一书。该书的主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John Berg教授,于是我估计到他应是审稿人之一。后来我们熟悉了,他寄给了我一份他撰写、签名的书中的一章(图5)。 图5. John Berg教授赠送给我的他撰写、签名的书中的一章
Rosenholm教授的课很有意思,他教的几门课都是无书的,采用现编的讲义。还记得他给我们大约10个人左右上过一门课,名字叫Dispersion,上到最后就剩我一个人了。于是我笑着对他说“看来我们还是结束课程吧,你安排我考试吧。”他莞尔一笑说“OK”,这课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有一门博士课程,是关于先进测试技术的,时间是一周。上课的五个老师分别来自赫尔辛基理工、赫尔辛基大学、芬兰科学院、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Rosenholm教授安排我去听这门课。因为主办方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招待所已经没有空余房间了,于是他为我订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这对于一个在读博士来说,还是极为奢侈的。这个课程的强度极大,但很锻炼人,每天听课、看相关的文章,然后自己做一个汇报,有点小答辩似的。最后回到我自己所在的学校时,带回了两大本厚厚的活页文选。在接下来一周的某一天,突然通知我进行考试,从赫尔辛基那儿传真考卷过来,我一个人进行闭卷考试,有一人进行监考。考完后,试卷再传真返回赫尔辛基。 Rosenholm教授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拿项目能力很强,我在他那里的第二还是第三个月就开始给我资助了。而且,他对我是完全放开式的散养模式,任凭我自己设计一个个的实验,最后形成完整的博士论文体系。而他则根据我的实验数据为我申请并获得了一个芬兰政府的大项目,类似我们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里的重点专项。申请的过程至今我还记得,1995年上半年,我先是被通知去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给芬兰的专家委员会做一个汇报,并回答了评委们的几个问题。然后在夏季放假前系里组织的一次郊外活动上,Rosenholm教授突然走到了我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用手摸着我的膝盖说:“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项目批下来了,这是我们物理化学系第一次将胶体和表面化学应用于制浆造纸技术,得到了政府的重点项目资助,谢谢你。”我顿时茫然不知所措,赶紧下意识地双手扶起教授。那年,这个项目有几百万芬兰马克,他因此为我组建了一个课题组,招了几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指导了其中的一个硕士和另外两个的实验和论文初稿的写作。因为有Rosenholm教授的支持,我大概是这个系里唯一一个不需要进行每周汇报的人,但也因此我写的论文都被他压下了。他很直接地告诉我,他需要我负责课题组,如果我的系列论文都发表了,就意味着我要拿到博士学位走人了。所以,那个阶段,我老是一个人出去开国际会议,每次我问他一起去吧,但是他都让我独自一个人去。于是,我去了加拿大、美国、葡萄牙等国,参加了好几场国际会议。到了1998年,我急着毕业,于是又找Rosenholm教授商量我的毕业问题。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了,于是同意我发论文。到10月份,发出去的文章基本上都被接受或发表了[1-9],于是他同意我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年(1998年)我获得了物理化学系发论文的冠军,奖品是一只芬兰出产的扁花瓶(图6)。好像多年后我仍是有史以来的年度发表论文第一名。1999年是我的博士后阶段,我和Rosenholm 教授一起完成了一些书的章节和会议论文[10-12]。 图6. 1998年,我获得的奥博大学物理化学系年度发表论文冠军的奖品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1998年10月底[13]。1998年12月21日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间也是我自己提出的,因为我的课程学分早已经完成了,而到这年10月份,我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已经超额完成了。当然,所有的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文件规定进行的。 时光荏荏苒苒的过去有好多年了,但至今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及过程中的那些事。 审核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外校教授中有两位来自瑞典的高校。离答辩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有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用芬兰语和瑞典语两种语言在芬兰的主要报纸和学校的报纸期刊上,预先报道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事,配了我的照片。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公示论文的作者、导师、答辩时间、地点、学位论文题目和研究内容摘要。所以,答辩那天有本地不同地方来的人,还有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来的人。 学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许多明文规定,其中有专门的答辩着装要求,有两种服装可以选择。首选是全黑的燕尾服,内穿相应的小领白衬衫,系白色领结,下身穿黑裤子、黑皮鞋;第二种是深色全套西装,领带领结都可。选哪种答辩服必须事先告知学校,以便届时主持答辩的教授们与答辩者的着装保持一致。此外,主持答辩的教授们还必须手持一顶圆筒型的礼帽(图7),这是博士学位拥有者的标配,一般人没有的。考虑到燕尾服平时穿不上,去租的价格极高,所以我是在当地买了全套的黑色西装和白色领结(图8)。 图7. 着正装,戴礼帽,主持答辩的教授们(取自网络)
图8. 博士论文答辩当天,我在系门口拍了这张照片,墙上系里工作人员的照片中,我右手边的就是Rosenholm教授
主持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教授来自赫尔辛基理工大学,他个子很高,高出我半个头,至少1米85。那天答辩结束后,我们一起合了照(图9),他告诉我他去过我们的首都北京,因为他也有着马克思一样的长髯,所以在北京有人说他像马克思。 图9. 主持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教授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学校最大的一个阶梯教室公开进行的,答辩前,参加的人都预先进入了教室。等我和主持答辩的教授们排队从后面进入时,全场起立向我们行注目礼,答辩结束后,大家排好队从我的左手边依次向我走来,一一握手祝贺。 那天,学校校长派他的秘书送来了一大捧献花和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对我的祝福(图10)。
10. 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当天校长送的明信片
系里的同事们除了送了我一张集体签名的贺卡(图11),还送了一件有意思的礼物,一个可以挂西装的包袋。 图11. 同事们送的签名贺卡
也还记得我和Rosenholm教授之间的许多往事,尤其是在他那里的最后一年做博士后期间的一次长时间的讨论。那是下半学期的一天下午,我俩约在会议室进行我的一篇论文的讨论,因为涉及不少公式,所以许多内容都是在黑板上进行讨论的。讨论的最后,他说这篇文章你作为独立作者投稿发表吧。该论文的接受很快,待我2000年初进入东华大学任教时,已经在Langmuir上正式发表了。里面我提出了一个假设,水的酸碱比大概为2.42。那时,源自JACS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的系列论文及讨论,国际上对此的讨论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后来,有人在文章中把这系数命名为“Shen系数”。Rosenholm教授也在他的一系列综述里反复提到了这个我读了至少几百篇英语论文得出的假设。该假设的其中一个应用点是对一系列高分子材料路易斯酸碱性能的评估。但遗憾的是我至今想不出合理的实验论证方法论证2.42的正确性,也只能一直默默地关注国内外关于水的研究,希望有人能用实验证明我的假设。 在奥博大学物理化学系里,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图12),是那时系里仅有的三个外国留学生在一起拍的。穿格子衬衫的姑娘Laura Ciovica来自罗马尼亚,黑衣的Hazel Watson来自英国,和来自中国的我。前者是跟我的,她后来拿了一个副博士移民加拿大了,后者博士毕业后结婚留在芬兰了。芬兰的副博士与博士学位之间仅仅差在没有正式发表的论文。当年系里为我定制的名片还有几张被保留着,统一的系标、色彩配置(图13)。
图13. 当年系里为我定制的名片
当然,还记得与系里同事们一起去欧洲其他高校进行的学术访问和交流,尤其是在瑞士的苏黎世联邦工学院(ETH)进行的那场访问(图14)。因为在那里,在一个有新民晚报那么大、至少有10公分厚的本子上签了名。此前,我只在奥博大学入校时,在如此大、如此厚的本子上签过名和写自己的简介。 图14. 这张在ETH的拍摄照片里(1997年),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现在,这里面的人有好几个已在芬兰、瑞典、德国等国的大学里任教授了
在东华大学高分子系工作期间,我花了十年时间,先后编写了《分子酸碱化学》(80万字,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2,ISBN 978-7-5439-5230-0),《高分子表面化学》(50万字,科学出版社,2014,ISBN 978-7-03-039525-2)、《高分子物理化学I》(50万字,科学出版社,2016,ISBN 978-7-03-047457-5)和《现代胶体化学》(35万字,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22,ISBN 978-7-5439-8570-4)四本书(图15)。希望为高分子和化学领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辜负Rosenholm教授对我的期望。 图15. 我编写出版的几本书
[1]Shen, Q. et al. Holzforschung 1998, 52(5), 521-529; [2]Shen, Q. et al. J. Colloid Interface Sci. 1998, 206(2), 558-568; [3]Shen, Q. et al. Colloid Surf. A 1998, 145(1/3), 235-241; [4]Shen, Q. et al. Colloid Surf. A 1998, 133, 261-268; [5]Shen, Q. et al. Nord. Pulp Paper Res. J. 1998, 13(3), 206-210; [6]Shen, Q. In: TAPPI Proceeding of 1998 International Chemical Recovery Conference, June 1-4, Florida, USA, 1998. TAPPI Press, pp. 1041-1044; [7]Shen, Q. et al. In: Proceeding of 5th European Workshop on Lignocellusics and Pulp, Aug. 30-Sept. 2, University of Aveiro, Portugal, 1998. pp. 179-182, ISBN 972-8021-66-6; [8]Shen, Q. et al. Kemiallisen massanvalmistuksen uudet haasteet-vuosiseminaari (KUMOUS seminar),4p., Hanasaari, Helsinki, 1998; [9]Shen, Q. et al. In: Abstract book of 1th Chinese scholar in Finland, Dec. 1998. University of Helsinki, Helsinki, Finland) [10] Shen, Q. et al. In: Advances in Lignocellulosics Characterization. Ed. D. S. Argropoulos, TAPPI Press, Chapter 10, 1999. ISBN 0-89852-357-5; [11]Shen, Q. et al. Wood Wisdom, Raportti 1/1999, Helsinki, 1999, 4p; [12]Shen, Q. et al. In: Proceedings of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od and Pulping Chemistry, II, 258-263, Yokohama, Japan, June 7-10, 1999); [13]Shen, Q. Interfac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od and cooking liquor in relation to delignification kinetics. Åbo Akademi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52-12-0337-4.
郭明雨,姚琳通 编辑 转载自“旦苑晨钟” |